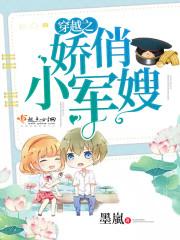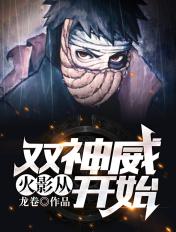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贫道要考大学 > 第192章 你俩的桌子和椅子成一套了(第2页)
第192章 你俩的桌子和椅子成一套了(第2页)
“必须找到她。”陈拾安站起身,抓起雨衣,“她在等一个回应,而不是同情。”
阿岩拦住他:“外面下着暴雨,你现在出去太危险!而且我们连具体地址都不知道!”
“我知道。”陈拾安从信封夹层抽出一张极小的纸片,上面印着一串二维码,“她贴在信纸背面,应该是从某个监控死角偷偷扫下来的。这可能是她唯一能接触到的外部网络入口。”
他用手机扫描,跳转至一个加密聊天页面,昵称是“困在春天里的蝉”。最后一条消息发送于两小时前,内容只有三个字:
**救我。**
系统显示定位在S市西郊纬七路18号,正是“阳光家园”社区B区3栋地下储藏室群。
“走。”陈拾安穿上靴子,顺手抄起角落里的强光手电筒,“带上便携录音仪和应急电源。如果真如信中所说,那里有实时监控上传,我们必须切断信号再行动。”
雨夜里,车子如幽灵般穿行在城市边缘。街道空旷,路灯昏黄,偶尔有自动驾驶清扫车缓缓驶过,机械臂挥动着刷子,像某种冷漠的守卫。
抵达小区时已是深夜。他们绕到B区后侧,避开主入口的人脸识别闸机,翻过一段矮墙。按照地图指引,3栋的地下室位于楼体西侧,原为物业杂物间,近年被改造为“家庭心理支持仓”,对外宣称提供“沉浸式情绪疗愈体验”。
“听着。”陈拾安压低声音,“别碰任何带摄像头的东西。这些设备可能连接云端AI,一旦识别出陌生面孔,会自动触发报警并锁定区域。”
他们撬开一扇锈蚀的通风口铁栅,钻入狭窄的管道。爬行十余米后,落地在一个堆满旧家具的隔间。前方一道金属门紧闭,门缝透出微弱蓝光。
陈拾安贴耳倾听,隐约传来电流嗡鸣与人声诵读的混合音:“……我很幸福,我没有烦恼,我爱我的爸爸妈妈……”
重复,机械,毫无起伏。
他掏出干扰器,轻轻按下开关。三秒后,走廊尽头的监控指示灯由红转黑。
门未上锁。推开刹那,一股霉味混着消毒水气息扑面而来。房间不大,约十平米,四壁刷成刺目的白色,中央摆着一张单人床,床上坐着一个瘦弱的女孩,正面对墙壁上的液晶屏,一遍遍复述着那句“幸福宣言”。
她听见动静,猛然回头,眼神先是惊恐,随即凝固成难以置信的震动。
“你是……陈拾安?”她的声音沙哑,像是很久没说过话,“我在视频里见过你。”
陈拾安蹲下身,与她平视:“我是来听你说实话的。你可以哭,可以骂,可以说你恨所有人。在这里,不需要表演快乐。”
女孩嘴唇颤抖,终于崩溃般地抱住膝盖,呜咽出声:“我不想‘治好’了……我只是想回家,哪怕只是坐在阳台上看看云也好……”
阿岩迅速检查房间设备,确认无隐藏摄像头后,启动便携录音仪。
“我们会带你出去。”陈拾安轻声说,“但在此之前,你能告诉我们,是谁帮你发的那封信?”
女孩摇头:“我不知道。那天半夜,音箱突然黑屏,门开了条缝,一封信滑了进来。我听见外面有人说了一句:‘别放弃说话的权利。’然后就没了声音。”
两人对视一眼。显然,内部已有觉醒者开始反水。
他们用毯子裹住女孩,从原路撤离。刚翻出围墙,远处警笛骤响。一辆巡逻车正朝这边驶来。
“走!”陈拾安抱起女孩冲向车辆。轮胎在湿滑路面打转,引擎咆哮着撕破雨幕。后视镜中,几道手电光柱在楼宇间交错扫射。
回到“倾听角”,医生连夜为女孩做了初步检查。除严重营养不良与睡眠剥夺外,未发现明显身体创伤,但脑电图显示前额叶活跃度显著降低??典型的长期精神控制后果。
“她需要时间。”医生离开前说,“也需要安全的环境,不能再让她感到被监视。”
陈拾安点头,安排她在附近一处保护性住所暂住,并指派专人陪伴。同时,他将此次营救全程录音整理成文,命名为《第七只萤火:关于一个被系统判定为“不快乐”的孩子》。
第二天清晨,这篇纪实文章连同女孩匿名绘制的“地下室日记”漫画一同发布。短短六小时内,转发量突破百万。无数家长留言:“原来我们也曾这样对待过孩子。”“我以为买个情绪监测仪是在关心他,没想到是在审判他。”
舆论再次沸腾。教育部紧急发布补充通知,严禁任何形式的私人AI系统参与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评估,并责令各地清查家庭智能设备滥用现象。
而就在此时,一封匿名邮件悄然抵达陈拾安个人邮箱。
发件人仍是那串乱码ID,标题只有两个字:**忏悔**。
正文写道:
>我是“家庭守护者”语音模块的原始训练师之一。你们救出的那个女孩,她的声音样本曾被用于优化“叛逆倾向识别模型”。我当时以为这只是技术迭代,直到有一天,我听见自己的女儿在家里对着空气说:“爸爸,我今天笑够了,你可以奖励我了吗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