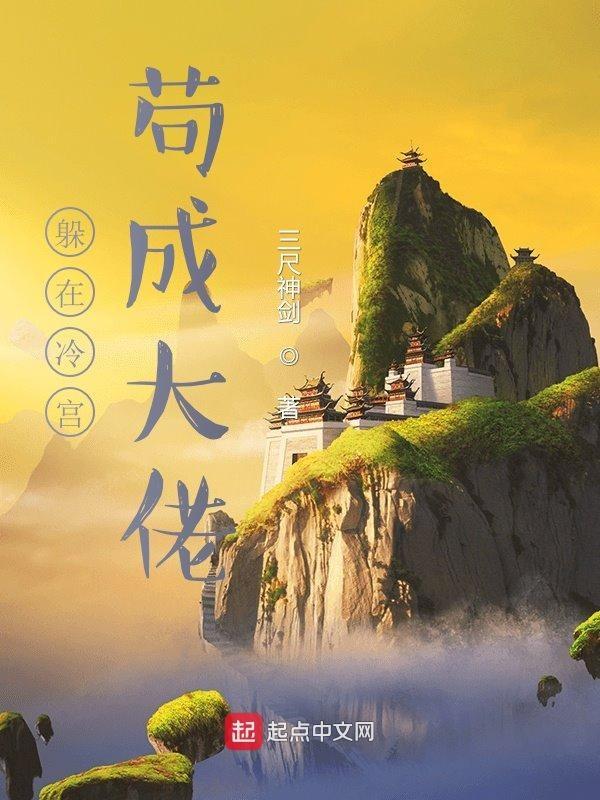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情迷1942(二战德国) > 小兔不见了(第4页)
小兔不见了(第4页)
这念头刚冒出来,他猛地直起身,冲到车尾,蹲身看车底,只有碎石和机油,又绕到车尾,掀开后备箱,空的。
被抵抗分子掳走了?
不可能,整场交火都在他掌控中,没人能接近这辆车。
“上校?”舒伦堡捂着胳膊走过来,“文医生她……”
“找。”男人打断他,声音冷得像冰,“她吓坏了,可能自己跑出去躲起来了,废墟,巷子,地下室,每一个能藏人的地方,找。”
“是。”舒伦堡怔了怔,便转身下达指令。
话音落,君舍已走向最近的一处废墟,半塌的咖啡馆,桌椅翻倒,杯子碎了一地,他蹲下身,手电光柱粗暴扫过每一个角落,掠过吧台,掠过楼梯,掠过堆着杂物的储物间。
没有,连一点布料勾挂的痕迹都找不到。
小兔胆子小,会躲到有遮蔽的地方,他手指无意识收紧了,像受惊的啮齿动物,会本能地钻进洞里。
“小女士?”他对着幽暗的走廊深处喊,声音里裹着一丝自己都没察觉的紧绷,“出来,安全了。”
回应他的只有玻璃碎片在脚下的咔嚓作响。
他直起身,大步走向街角的绿色铁皮垃圾箱,一把掀开箱盖,只有几只老鼠吱吱乱窜,旁边的报亭金属框架被他掀起又重重砸下,哐当巨响在空荡的街道回荡,扬起一片呛人的灰尘。
空的。
理智像一根被不断拉扯的弦,发出危险的嗡鸣。到底去哪了?
士兵们陆续从各个方向折返:“东侧没有。”“西侧没有。”“巷子里看了,没有人。”
君舍没说话,步伐却比刚才快了些,旁边是栋残破的公寓楼,底层窗玻璃没了,里面是间被洗劫过的客厅,家具翻倒,墙上有弹孔。
“文医生?”他喊。
死寂,只有自己的呼吸声,他踢开卧室门,衣柜洞开,空的,厨房碗碟碎了一地,也是空的。
洗手间,门关着。君舍握住门把的瞬间,心脏莫名跳快了一拍,会不会躲在里面?害怕得捂住嘴一声都不敢出?
门轴发出艰难的吱呀声。
浴缸里积着锈红的污水,镜子碎了一半,残片映出他半张阴沉的脸。没有温度,没有气息,连水龙头滴答声都没有。
君舍站在门口闭了闭眼,她肯定在附近某个地方,只是吓坏了,不敢出来。
当他踏出公寓楼时,舒伦堡迎了上来,脸色比刚才更难看了:“上校……这一带都搜过了,没有。”
君舍停下脚步,没说话,但他的眼神让舒伦堡脊背发凉,那里面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悄然裂开。
“继续找。”君舍说,声音很平,“每一栋建筑,每一个地下室,每一个能塞进兔子的洞。”
“可是上校,这附近建筑太多了,很多结构不稳,”舒伦堡硬着头皮。“我们人手…。”
“继续找!”
男人声音陡然拔高,不是吼,倒更像是某种更原始的、近乎嘶哑的东西。
舒伦堡浑身一僵,所有到嘴边的话尽数咽了回去:“是!”
士兵们再次散开,像受惊的蚂蚁,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凌乱地响起来。(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