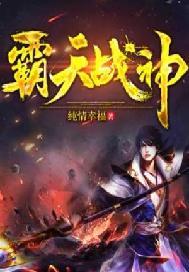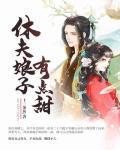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文娱2000:捧女明星百倍返利 > 第411章 主动的安妮公主(第2页)
第411章 主动的安妮公主(第2页)
而文弟当时批注了一句:“正是这种无需台词的真实,才最接近生命的本质。”
他将这段视频上传至“真实数据库”,标记为“001号原始样本”,并设置权限:仅限非遗研究机构及立法部门调阅。
三天后,中科院联合团队传来好消息:新一代记录仪重量成功压至一百四十三克,外壳采用航天级碳纤维复合材料,可在零下六十度环境中连续工作九十小时。更关键的是,内置芯片新增“生命信号捕捉模块”,可通过分析拍摄者的心率、体温、语音震颤等生理数据,反向验证记录行为的真实性。
“我们可以证明,”工程师在邮件中写道,“这不是一段被操控的表演,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,在特定时空下,用身体感知世界的痕迹。”
夏日渐深,项目推进如潮。
六月中旬,第一批“大地之声”学员完成集训,奔赴全国各地。他们中有内蒙古草原上的气象观测员,带着微型摄像机记录每年迁徙候鸟的第一声鸣叫;有贵州侗寨的鼓楼长老之女,立志用十年时间还原整部《萨岁史诗》的吟唱全过程;还有一个甘肃敦煌附近的护窟人儿子,从小听着父亲讲解壁画长大,如今要以民间视角拍摄“普通人眼中的莫高窟”。
文弟为每人定制了一枚铜牌,正面刻着“看见即抵抗”,背面则是他们的编号与誓言手迹。
与此同时,《光在雪上》冲击奥斯卡进入最后阶段。国外评委陆续发表评论,称其“以极简美学重构了纪录片的伦理边界”。更有权威影评人撰文指出:“这部影片没有英雄叙事,没有悲情渲染,但它让观众意识到:所谓尊严,并非来自被拯救,而是源于不被忽视。”
然而就在提名公布后不久,一股新的舆论暗流悄然浮现。
某境外文化评论网站刊发长文,题为《被浪漫化的苦难:中国纪实影像的政治隐喻》。文章声称,《光在雪上》刻意回避社会结构性问题,将贫困美化为“诗意生存”,实则是“国家软实力输出工具”。
国内部分自媒体迅速转载,标题愈发耸动:“文弟是不是在消费穷人?”“那些感动全世界的画面,是不是精心设计的宣传?”
压力再度袭来。
这一次,文弟依旧选择沉默。但他做了一件事??邀请十位最初参与《光在雪上》拍摄的村民代表,赴京参加一场闭门放映会。
这些人里有央金的丈夫扎西,有片中那位抢救土墙房的苗族老人,也有达普洛村小学的校长。他们从未坐过飞机,有些人连县城都没去过。抵达当晚,公司安排他们住在协和医学院附近的招待所,每人发了一部平板电脑,预装了影片的所有幕后花絮与原始素材片段。
次日上午,放映会在一间小型报告厅举行。没有主持人,没有致辞,只有投影仪亮起,画面缓缓切入第一场戏:清晨五点,央金背着药箱走出家门,雪地上留下一行孤独的脚印。
当看到自己出现在大银幕上时,扎西低头搓着手,一句话没说。而那位苗族老人则几次抹眼泪,喃喃道:“原来那天拍完,你们还帮我把墙撑住了……我以为你们走了。”
放映结束,文弟请他们谈谈感受。
扎西第一个开口,普通话生涩却坚定:“有人说你们拍我们是为了赚钱、为了拿奖。可我知道,那年冬天我发烧四十度,是你们的卫星电话联系上的救援队。你们走的时候,连一口酥油茶都没多喝。”
老人接着说:“我那房子塌了也没关系,反正快死了。可你们拍下来以后,县里派人修了新房,孙子也能安心上学了。要是这叫‘消费’,那我宁愿被消费一万次。”
全场静默。
最后是校长发言:“孩子们看完电影后,开始写日记了。以前他们只会抄课文,现在写‘我想当医生’‘我要建电站’‘我不想逃婚’。你们给了他们一种东西??希望。这不是宣传,是命。”
会后,这段对话被整理成文字,配上现场照片,发布在“火种档案”公众号。没有任何辩解,只有原声直录。
舆论风向悄然逆转。
一周后,“#真实不需要辩护#”登上热搜榜首。有网友发起接力活动,上传自己家乡普通人的日常影像:新疆果农采摘葡萄时的笑声、重庆棒棒军扛货上楼的喘息、广西瑶族妇女织锦时的眼神……短短三天,相关视频播放量破亿。
而在此期间,文弟已悄然启程前往西藏。
他要去见央金。
车子翻越唐古拉山口时,天空骤然变色,乌云压顶,雪花夹着冰粒砸在车窗上。司机紧张地握紧方向盘:“这种天气,牧民都不会出门。”
文弟望着窗外茫茫雪原,忽然说:“但她会。”
果然,抵达那曲镇外最后一个检查站时,哨兵指着远方一条模糊的身影说:“那个女医生,一个小时前进山了,说是去给一家三口打疫苗。”
“哪家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