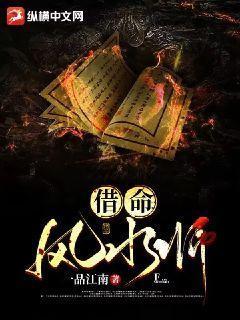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赵尔丰:雪域将星梦 > 第十二章 历史夹缝中的抉择(第2页)
第十二章 历史夹缝中的抉择(第2页)
“那好。本帅这就找凤山谈。留不留,以他个人意愿为定。”看傅华封连连点,赵尔丰又说:“时不我待。我明早即起程回川,届时万万不要张扬,以免军心摇**,你等更是要以身作则,切切不要前来送行。”尊敬不如从命,傅华封当即唯唯连声,适时起身告辞。
橐橐橐,熟悉的牛皮战靴声传进耳鼓,一听这熟悉的脚步声,就知是凤山来了。赵尔丰,降阶迎接,算是殊礼。
“大帅!”风山趋前一步,向赵尔丰拱手行礼。
“请。”赵尔丰亲热地执凤山手,让进客厅。
“大帅先请!”凤山坚持要赵尔丰先行,他们相跟着进了大帅行辕的小客厅。其时,夜幕已弥漫室内,弁兵给客人上了酥油奶茶,又在旁边燃得正紧的枝子形黄铜灯架上再添一只大红蜡烛,点燃后,看大帅再无吩咐,轻步而退,并轻轻关好门。
赵尔丰看着在明亮在烛光下始终保持着军人风纪,正襟危坐的凤山好半天没有言语,心中不禁泛起感情的涟漪。
不管什么时候,凤山都保持着职业军人的特征。他高高的个子,黑红的脸膛,身躯结实魁梧。身穿得胜褂,腰上系宽宽的皮带,右手紧执刀柄。伞形红缨帽下,一张有棱有角的脸,神态沉稳。此时,他坐着这儿,坐姿如青松,神情磐石般镇定。特别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凤山那双眼睛,有种钻透力。现在他一如平时,寡言少语,安安静静,像一个腼腆的姑娘,准备接受大帅的垂询。而一旦上了战场,凤山立刻变了一个人,身先士卒,呼啸呐喊,勇敢杀敌,攻无不克,战无不胜,像一只威风八面的雄狮。
“风统!”赵尔沿袭着边军中大都官兵对凤山的称呼,用这样的称呼显出别样的亲切:“你跟我南征北战有十年了吧?”
“是”。凤山点点头,他的话很少。赵尔丰眼中透出一丝犹豫,更多的是关切:“明天我就要回成都去了,对于你的去留,我拿不定主意。你知道,康地需要你,我身边也需要你。你看你是跟我去川省带兵,还是就留在康区主持军事?”
“全凭大帅调遣,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”
“难得!”赵尔丰心中不禁涌起大波,霍地站起,在室内来回踱步。一时,他有些踌躇。从内心讲,他很喜欢这个年青有为,身经百战的将领,很想把他带回去。但康区目前更需要他。他在边军中的威望比傅华封高得多。况且,目前好些将佐兵士都想回川省。将凤山留下,可极大地稳定军心。想到这里,赵尔丰决定了,赵尔丰重新坐下去,看着风山,说了一番话,很真诚也很动情:“凤山,你素来深明大义。说真话,我是很想带你回去,因为目下川局也急需你这样的军事人才。然而,我前脚走,藏军必然西犯。藏军背后有英人支持,不断得到新式武器补给,接受英国人的训练,战斗力日益得到加强;华封毕竟是一介文人,谋划可以,但临阵指挥,难望风统你的颈背,他军事上不如你。康区不稳,不仅川局动**,进而会西南摇撼,甚而动摇社稷!因而,我思虑再三,想委屈你在康区再带一段时间的兵。不知尊意如何?反正,以尊意为是。”说完,看着近咫尺的凤山。
“大帅放心!”凤山说出的话掷地有声:“凤山是军人,忠君报国是军人的本份。好男儿当马革裹尸还。风山在此向大帅保证,一定率边军,像钉子一般守牢西部边陲。有大帅一番话,凤山一腔热血,愿洒在康区!”
“血不要洒在康区,凤统!”赵尔丰动了真情,殷殷叮嘱爱将:“你既要打胜仗,又要保存自己。”看风山点点头,赵尔丰又站了起来,在地上踱了两步,拂髯长叹,不胜唏嘘:“朝廷有幸。有凤统这样的忠臣良将镇守康区,西南边陲稳如磐石矣!”
看没有了事,风山这就适时站起,向大帅告辞。
“且慢。”赵尔丰说时走到书桌前,就着红烛,提笔展纸。只见他笔走龙蛇间,写下了“疾风知劲草,板**识忠臣”八个大字送给凤山――赵尔丰今晚送凤山的条幅写得丰神峻骨,回肠**气。
“俗话说得好――千里送鹅毛,礼轻情义重。”赵尔丰说:“明天我们一早就要走了。算起来,我们共事前后已有十年,临别我送你两样礼物:一是写这个条幅送你。这既是对你的气节写照,也是我们的共勉。二是我将我的爱马‘追风青骢’马送你,作个纪念。”
“万万不可!”凤山连连摇手:“大帅的墨宝我愧领了。宝马万万不能要!这宝马是钟(颖)协统送大帅的。”
“凤统!俗话说得好,小场子难跑骏马,花盆养不出万年松。‘追风青骢’应该属于将军、应该属于康区辽阔的雪山草地。希将军不要推辞,请接受我的一片心意。”说着挥挥手,示意凤山不必再推辞。末了,赵尔丰将凤山一直送出中门。
晨曦刚刚露出鱼肚色,巴塘还在最后一线夜幕中沉睡。城郊川藏路上已响起一串经久不息的嗒嗒马蹄声——新任四川省总督赵尔丰带着他的卫队和纪得胜营悄悄出了城,上了官道。毕竟是训练有素的边军,令行禁止。昨天晚上赵尔丰就对傅华封说好了,并三令五审,不准任何人前来送行,包括傅华封本人。今天早晨确实如是。
巴塘已甩在身后两三里地,忽听背后传来一阵熟悉的咴咴骏马嘶叫声。
“啊,是大帅的‘追风青骢’马追来了!”……
官兵们不由得欢呼起来。赵尔丰不禁一惊,调头勒马看去。只见“追风青骢’披着淡淡的晨曦,像一支利箭,从后方射来,端端射到东去的军队前方,用一个漂亮的战术动作,截着了队伍。再顺着队伍像一朵彩云似地飘了过来,来在赵尔丰面前,“追风青骢”两只前腿支起,后腿立地,立成一个人字,咴咴两声中,风山滚鞍下马,站在大帅面前。
“凤山你来干什么?”赵尔丰佯怒,手指凤山责备:“我再三声明,不准将士前来送行,你身为统领,却如此带头不执行命令?”
“大帅息怒!”凤山说:“大帅不准送行的命令,昨晚就已传达全军。然,当大帅刚走,‘追风青骢’却咴咴嘶叫长鸣,似泣血不已。马通人性,凤山心觉不忍,特陪它来送大帅一程。”
赵尔丰长叹一声,跨下马来,上前两步,手抚“追风青骢”:“成都没有你驰骋的地方,你就留在你的家乡――大草原上吧,跟着凤山统领,保卫乡梓,我们后会有期!”说罢,重新上马。也真是奇怪,“追风青骢”似乎听懂了赵大帅的话,咴咴长啸两声,调过头去。
“大帅保重!”凤山拱手说了这一句,似乎不忍卒别,猛地跳上“追风青骢”。嗒嗒嗒,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响过之后,凤山连人带马消失在曙光初露的草地尽头。
赵尔丰勒转马头,率领纪胜营,在卫队的前后护卫下,披着晨曦,迎着初升的太阳加紧东行。
过了泸定,越往东走,地势越渐平坦,人烟越见稠密,土地越见膏腴,部队士气越见高涨。五天后,赵尔丰一行翻越险峻的大相岭,又行两日到达雅安。那是中午时分,拐过一个山头,蓦然间,天高地阔,久违了的青山绿水,平畴沃野和着万瓦鳞鳞的城郭,在暮春的朗朗阳光下一齐扑进眼帘。身居康藏七年的五百多名官兵见状,先是一惊,继而一个个睁大了眼睛,大有如在梦中,云游天堂,今昔何昔的恍惚感,待始信是实时,都欢呼起来,有的更是喜极生悲,一下跪在沃土上,潸然泪下。
赵尔丰大帅也自觉眼睛一亮,情绪受到感染。不禁勒着马缰,拂着颔下银须,在充满绿意的阳光下,眯缝起眼睛,眺望着久违了的内地风光,不胜唏嘘。想当年随自己出关的傅华封、凤山等多营边军官兵还留在水瘦山寒的康区戎边卫国,心中感慨莫名。
一阵嗒嗒的马蹄声将赵尔丰从沉思中唤醒。抬起头来,只见管带纪得胜在自己面前滚鞍下马,拱手禀报:“大帅!川省派出的代表饶凤藻等人,早两日到雨城迎候大人。现已在城外摆好香帛迎侯大人了!”
“好!”赵尔丰勒过马头,情不自禁地掸了掸自己身上穿的得胜褂,再拢拢头上戴的饰有一品顶戴的伞形红缨盔帽,朗声命令:“各队整好衣冠,排好队形,两路纵队,随我进城。”
过了金鸡关,一马平川的富饶的川西平原便尽现眼前。无边无际的绿野平畴,蛛网般的水渠,浓荫掩隐的林带,袅袅的炊烟……愈往东行,愈给人一种美不胜收之感。川藏线也陡然变宽了。然而,赵尔丰一行反而走得慢了起来。不是别的,只因在饶凤藻等川省代表坚持下,新任总督大人赵尔丰乘上了八人抬绿呢大轿,抠起了架子,讲起了排场。一路上州官、县官鸣锣摆香帛接送、叩拜、庶民回避,数不尽的繁文褥节。雅安到成都不过三百来里平洋大坝,所经之处,不过雅安、名山、邛崃、新津、双流五州县,赵尔丰却在第五天上午才到成都。
“总督大人,武侯祠到了!”当新任四川省总督赵尔丰乘坐的八人抬绿呢大轿,在一群翎顶辉煌的戈什哈护卫下,威风凛凛,旗幡招展,前呼后拥中来到成都南郊古柏森森的武侯祠前停下时,川省代表,未来的幕僚饶风藻趋步上前,挑起轿帘,轻声禀报:“川省所有大员都出城欢迎大帅来了!”
“嗯!”赵尔丰很矜持地哼了一声,轻提袍裾,缓步走下轿来——宣统三年(1911年、辛亥)闰六月十一日,在康藏经边七载,功勋赫赫的赵尔丰回到了久违了的成都。性情还是那样执拗。周身裹着塞外风尘的大帅,下轿伊始,对香帛前排列得整整齐齐,等着朝见的大员们视而不见,却转过身去,伫立轿前,借看川西风情掩盖内心的滚滚思绪。
成都附近的农村最具天府特色,有一种温柔富足的气息。远远,水平如镜的秧田中,有星星点点的农人躬着腰在插秧。一缕轻风从田野上滚来,传过农家小伙唱的栽秧忙山歌,极有韵味:“太阳下山月出山,照得黑夜变白天。晃醒了我家鸡娃子,叫得我,天还不亮又下田……”但赵尔丰知道,这不过是一种表象。自己捏在手上的决不是一个令人垂涎的红果子,而是如傅华封所说,是烫手的红炭圆!在这里,他再见不到二哥了。因为前任川督赵尔巽月前升任东三省总督,在朝廷催促下,等不及三弟来接任就走了。在任总督不等新任总督来办交接就走,这在清廷历史上,也是从未有过的事啊!可见局势之严峻。二哥临走前给他留了一封信,算是新老川督的交接,也是哥哥对弟弟的忠告。二哥在信中谈了蜀中危机四伏的局势,指出关键是要解决好川人的保路运动。至于如何解决才好?对此,二哥没有提出明确的对策,只是再次引用了前人箴言:“天下未乱,蜀先乱,天下已治蜀后治”,这无异是提醒他,主持川政,切切要审时度势。
“大人!”饶凤藻趋步来在身边,打断了他的沉思,轻声提醒道:“朝拜的大员们已等候大人多时。”
“嗯!”赵尔丰这才转过身来,走上前去,以他素常傲慢的姿态,接受川省大员们的朝拜。其中惟一引起他注意的是一位高个子军官。很年轻,相貌很是英武,漆眉亮目,声如洪钟,英气逼人,态度不卑不亢;他想起二哥在给他的信中,对蜀中俊杰逐一介绍时,提到过的尹昌衡;说这人虽然今年才只有二十七岁,但在川军中威信很高。二哥在信中特别嘱咐他注意,说尹昌衡是个不成龙便成蛇的人,万万不可小视……
“唔,这娃娃是哪个?”他让师爷送过手本清对。没有看错,就是他——尹昌衡。啥子那么凶,一个刚出世的新毛猴嘛!自视甚高的赵大帅并没有太注意尹昌衡,草草结束了这礼节性的应酬,不胜其烦的赵大帅登上八人抬绿呢大轿,在前呼后拥中直奔督署而去。
人说赵尔丰办事操切,果然是。他上午刚到,下午就去了岳府街保路同志会。为了给蜀中士绅一个礼贤下士的好印象,他身着便装,青衣小帽,乘一顶二人抬小轿,跟班也只有一个师爷,另带一个穿便装的卫士——草上飞何麻子。
赵尔丰一进门就感到气氛火辣辣的不对。阳光透过嵌在雕龙刻凤的木窗上的花玻璃,洒在好大一间房内。房内坐了满****一屋的士绅们,因为激愤,这些士绅一改往日司空见惯的文质彬彬样子,争着发言,在大声武气地声讨邮传大臣盛宣怀、川汉铁路大臣端方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