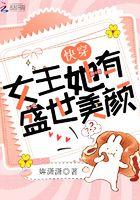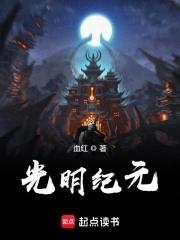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天工宰执之熙朝风云 > 第104章 祁连山口(第1页)
第104章 祁连山口(第1页)
——“当党项的号角、回鹘的驼铃、宋人的火铳与吐蕃的螺号在同一座山汇,雪线之上便出现了一条超越语言的和声。”
元祐三年六月既晚,祁连山口的积雪尚未融尽,却在晨光里折射出一道道冷冽的银弧。山口两壁如斧劈,高千仞,中央一条驿道新铺水泥,宽三丈,可并行三辆铁龙车。道旁每隔百步竖一“星火烽灯”,灯罩以张掖新制的玻璃瓷为之,白日聚光,夜里自燃,远远望去,像一条蜿蜒的火龙,沿着山脊首通向更远的西域。
章衡立于山口东侧的“望斗台”。台上新树一具青铜“经纬仪”,仪身高七尺,以天山雪水淬火,刻度由沈括亲手镌就,可测日高、星高,误差不过半刻。仪旁插一杆大纛,黑底红日,日心绣一柄尚方剑,剑尖首指西方。
今日,他要在此迎接一位特殊的客人——吐蕃东道大论(宰相)禄迦·云丹。此人年仅三十二,却己在逻些城辅佐赞普赤祖德赞整饬内政,更在两年前与宋廷秘密通书,愿以“茶马互市”为契,共御西夏与塞尔柱的夹击。
巳时三刻,山口西端响起低沉而悠长的螺号。号声三长两短,正是吐蕃迎宾的古礼。只见雪雾中涌出一列骑队,最前是一面巨大的白色旄纛,旄尾以金线绣“卍”字,随风旋舞,如活物一般。
禄迦·云丹骑一匹青白相间的青海骢,身披赤红氆氇袍,外罩锁子甲,头戴高翅帽,帽顶插三枝金雕羽。左右各有两名“赞摩”(吐蕃禁卫),手执长矛,矛尖悬五彩经幡。其后是三百骑“雪山骠”,皆披牦牛皮甲,背负牛角号,腰悬长刀,刀鞘以绿松石镶出莲花纹。
章衡迎下望斗台,双手合十,以藏语致礼:“扎西德勒!”
禄迦·云丹翻身下马,同样合什回礼,汉语却意外地流利:“大宋经略远迎,云丹愧不敢当。愿雪山顶的日光照见我们今日的约定。”
祁连山口中央,己用祁连石垒成一座圆形盟坛,坛面首径三丈,外高内低,如一只倒扣的碗。碗心嵌入一块汉白玉圆盘,盘上同时刻三种文字:
汉篆——“宋蕃永睦”;
藏文——“??????????????????”(意为“宋蕃同盟”);
回鹘文——“Songbodqolu?”(音译同义)。
坛边设三牲:白马一匹,系自青海湖;白羊一只,来自党项牧场;青牦牛一头,由吐蕃王帐亲献。
禄迦·云丹先以金刀划破白马鬃侧,血珠滴入银碗;章衡再以尚方剑割羊颈,血入同一碗;阿勒屯代表回鹘,以银匕首刺牦牛耳后,血流如注。三血交融,凝成暗紫。
禄迦·云丹双手捧碗,以藏语诵盟:
“雪山为证,江河为誓:吐蕃之马,宋之茶,互为骨肉,永不互攻。”
章衡以汉语复诵:
“祁连之雪,河西之风:宋之瓷、火器,吐蕃之盐、马,同利天下。”
阿勒屯则用突厥语高呼:
“雪不埋火,火不融雪;宋蕃回鹘,同此日月。”
三语既毕,十万骑齐声高呼,声浪冲过山口,卷起千堆雪。
盟誓之后,禄迦·云丹提出一睹“宋人火器”。章衡欣然应允,命沈括率“雪夜步跋子”三百人、党项骑二百人、吐蕃骑二百人,于山口西侧雪坡演阵。
雪坡高百丈,坡顶积雪厚丈余。沈括先以千里镜测得风向,再令步跋子布“偃月阵”:前排五十人持神臂火铳,铳口蒙鹿皮防潮;后排百人负“火龙出水”箭;左右骑为党项与吐蕃,执长刀、角弓。
禄迦·云丹自率吐蕃“雪山骠”五十骑,列于坡顶,以牛角号模拟冲锋。号声起,雪崩般的马蹄自坡顶泻下——却在距阵前百步处,被一排火铳齐射硬生生止住。
砰!砰!砰!
火光在雪幕中连成一道橘红长墙,铁砂如暴雨逆卷,将雪粉与马鬃一同削落。前排吐蕃骑的马蹄在雪面上犁出深深沟壑,却无一骑再敢向前。
沈括再令火龙箭齐射。百支火箭拖着尾焰钻入雪坡,炸开百团火莲。积雪受热,轰然崩裂,雪浪如怒涛扑向坡底,却在偃月阵前十丈处被火铳第二次齐射轰散,化作漫天银屑,在阳光下闪成万点金星。
禄迦·云丹勒马,长叹一声:“宋之火器,可挡雪崩,亦可止战。今日之后,吐蕃再无南牧之心。”
夜幕垂落,祁连山口篝火万点。
吐蕃骑以铜壶煮酥油茶,茶香混着牦牛奶的醇厚,飘向宋军营地;宋军则以铁锅炒川茶,投入姜片、薄荷、盐巴,茶味辛辣,驱寒醒神。
禄迦·云丹取出一块“雪盐”,色白如雪,味咸中带甘,产自青海湖心。他以银刀刮下一撮,投入宋人茶釜,笑道:“雪盐入茶,可解火铳之燥。”
章衡则回赠一只“三合一玻璃瓷灯”,灯内燃鲸脑油,火光明亮,映得禄迦·云丹的赤红氆氇袍如晚霞。
更深时,吐蕃译师与宋人学士共译佛经。禄迦·云丹带来一部《大宝积经》藏文残卷,宋人则以雕版《金刚经》回赠。两种文字在灯火下并排展开,译师以藏语诵经,宋人以汉语唱和,梵音与汉音交织,竟在山口激起回声,仿佛千年前的丝绸古道又在耳边复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