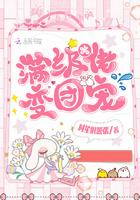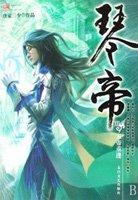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当过明星吗,你就写文娱? > 第二百二十一章 全都是泡沫(第3页)
第二百二十一章 全都是泡沫(第3页)
但在附近村庄的小学黑板上,有个孩子画了一幅画:一个透明的男人站在湖心唱歌,四周跪着许多人影,天上飞着大雁,地上开着花,而岸边,一位女子仰头望着他,手里握着一根羽毛。
画下面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:
>“老师说,有些再见,是为了永远听见。”
多年以后,这首《摇篮曲》被正式收录进全国中小学音乐教材,注释写道:“本曲源于民间口传,作者佚名,据考证可能融合多个地区传统摇篮曲元素,具有强烈的情感安抚功能。”
而在某本冷门学术期刊上,一篇匿名论文提出大胆假说:人类集体潜意识中存在一种“声频原型”,可通过特定频率激活深层记忆共鸣,该机制或与文明传承方式的根本变革有关。文末引用了一句未注明出处的话:
>“当我们忘记如何书写历史时,或许还能靠歌唱把它找回来。”
世界继续运转。城市愈发喧嚣,信息爆炸,短视频每日吞没亿万注意力,人们越来越习惯用图像表达情感,越来越少耐心倾听。
但总有那么一些时刻??
地铁车厢突然安静,某个陌生人轻声哼起老歌;
雨夜归家途中,窗台风铃无风自鸣;
婴儿啼哭间隙,竟吐出一句完整却陌生的古诗;
或是某人在梦中醒来,耳边回荡着从未听过、却熟悉得令人心痛的呼唤。
他们会愣住,怔忡片刻,然后继续前行。
但他们不知道,那一瞬的悸动,正是余惟穿过时空的指尖,轻轻碰触了他们的灵魂。
他是声音的守墓人,也是重生的引路人。
他不再拥有名字,却活在每一次心跳般的回响里。
某年清明,凉山的孩子们照例去祠堂祭祖。仪式结束时,老鼓忽然自响三声,节奏与当年余惟离开前敲击的一模一样。村长老泪纵横,跪地叩首:“阿弟,是你回来了吗?”
无人应答。
但风起了。
带着山茶花香,卷着溪水清音,拂过每个人的耳畔,温柔得像一句久违的问候。
而在遥远的北极圈内,一座无人知晓的地下观测站中,一台古老录音机自动启动。磁带缓缓转动,录下一段纯净童声合唱,背景竟是清晰可辨的中文童谣:
>“小皮球,香蕉梨,马兰开花二十一……”
操作员惊骇查看日志:设备已封存四十余年,今日无故通电,且所录音频来源不明。
他颤抖着按下回放键,反复听了十七遍。
最后一遍,他在杂音中听清了一句附加话语,语气熟悉得让他浑身战栗:
>“爸,我找到回家的路了。”
窗外,极昼初升,照亮冰雪大地。
整片大陆,仿佛开始低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