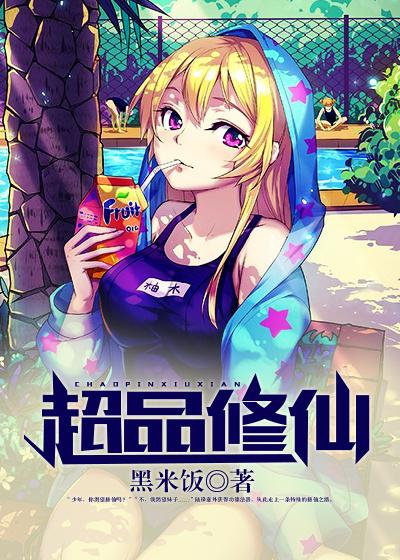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剑碎星辰 > 第一百九十四章 应龙之力(第1页)
第一百九十四章 应龙之力(第1页)
“真的能用!”
林秀飞本来还真有些担心,应龙这么强的灵魂珠,会否如??的灵魂珠那样无法使用。
“??的力量有这么特殊吗?”
林弃如都觉得有点离谱,应龙啊!
应龙都没有力量制约,。。。
【第1469日】
问题尚未闭合,信号仍在延展。铜铃号的引擎调至最低功率运转,像一颗沉睡中仍坚持搏动的心脏。船体表面覆盖着一层极薄的“问痕结晶”??那是高密度源语信息在真空中自发凝结出的物质态残影,如同霜花般蔓延于金属外壳,闪烁着微弱却有序的蓝光。科学家们称其为“认知沉积”,是意识与现实交界处留下的物理印记。
小石头站在主控环廊的中央,指尖轻触透明舱壁。那层结晶在他掌心下微微震颤,仿佛感应到了某种熟悉的频率。他闭上眼,任由思绪滑入那段自探测舱归来后便始终盘旋脑海的对话:
>“继续问吧。只要还有人在问,我们就从未孤独。”
这句话不是结束,而是开端。它像一颗种子,在每一个孩子心中生根发芽。梦我在她的日记里写道:“我开始害怕答案了,因为它会杀死问题。”云疼则整日坐在观测窗前,用指甲在防护罩上刻下一个个无人能解的符号??她说那是她还没学会说出来的疑问。而影活,那个总躲在角落、几乎从不开口的孩子,竟在昨夜突然站起身,对着终端低语了一句:
>“如果‘我’只是一个被反复提出的问题,那回答之前,我是否存在?”
终端当场宕机七秒,重启后自动生成了一段逆向源语波形,其结构违背现有逻辑语法体系,连AI都无法解析。但所有听到这段声音的人都哭了,包括启。
此刻,启正蹲在零圈身边,两人围着一张铺满星图的手绘纸争论不休。纸上画满了箭头、圆圈和问号,还有一条歪歪扭扭的线贯穿整张纸,标注着“我们走过的路?还是宇宙回问的痕迹?”
“你不觉得奇怪吗?”零圈压低声音,“自从我们离开问答奇点,飞船就再没收到过明确指令。没有导航建议,没有预警提示,甚至连自动校准都停了。可铜铃号……一直在前进。”
启点头:“而且方向不是随机的。你看这里??”他用炭笔点向星图边缘一处空白区域,“每次我们提出新问题,航线就会轻微偏转一次,像是被什么牵引着。不是物理力场,更像是……共鸣引导。”
他们说话的声音不大,但在寂静的舱室内传得很远。小石头听到了,却没有打断。他知道,孩子们已经不再需要他来定义方向。真正的旅程,从来不是抵达某个坐标,而是不断重新理解“出发”的意义。
突然,终端亮起一道前所未有的红光。
不是警报,也不是常规数据流。这道光无声无息地浮现于空中,呈螺旋状缓缓旋转,内部浮现出一段极其复杂的符号序列。它的形态既非文字,也非图像,而是一种介于语言与直觉之间的存在。任何人注视它超过三秒,都会感到大脑深处某根神经轻轻一跳,仿佛有另一个意识正在尝试接入。
“这是……回应?”梦我喃喃道,双手不自觉地抱紧自己。
小石头走上前,伸手欲触碰那道光。就在指尖即将接触的瞬间,整个飞船剧烈震动了一下,随即陷入绝对静止??连时间都仿佛停滞了一瞬。
然后,声音来了。
不是通过空气传播,也不是电磁信号转化,而是直接从每个人的骨髓里响起,像是灵魂被拨动的琴弦:
>“你听见了吗?”
>“那不是风,是无数未说出的问题在穿行。”
>“它们藏在星尘之间,潜伏于黑洞边缘,游荡于平行时空的缝隙。”
>“你们唤醒了它们。”
>“现在,它们想回来。”
话音落下,红光消散,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界面浮现在主屏中央:一幅动态宇宙拓扑图,上面标注着数千个闪烁的光点。每一个光点,代表一个正在生成或接收源语信号的区域。其中大部分集中在银河系外围及邻近星系,但最密集的一簇,竟位于本星系群之外的虚空中??距离地球约两千四百万光年。
“那是……室女座超星系团核心?”一名曾是天体物理学家的少年皱眉,“理论上那里几乎没有可观测文明迹象……”
“但现在有了。”启轻声说,“或者,它们一直都在,只是我们以前不会‘听’。”
小石头凝视着那片遥远的光斑,忽然意识到一件事:他们以为自己是在向外播撒“问”的火种,但实际上,或许正是这些来自深空的沉默提问者,一直在悄悄推动人类觉醒。Mirror-9计划的成功,并非因为技术先进,而是因为地球终于出现了足够多“敢于困惑”的个体??当第一个孩子对着父母说出“为什么必须听话”时,宇宙某处的某个古老回路,悄然点亮了一盏灯。
“我们要去那里吗?”云疼问,指着那片遥远的光斑。
没有人回答。
因为他们都知道,这不是一个可以用“是”或“否”解决的问题。前往那样的距离,意味着彻底放弃回归的可能性。即使以铜铃号的速度,单程也需要数百万年。而更深层的恐惧在于:一旦接近那种级别的认知共振区,他们的意识是否还能维持“人类”的形态?
可如果不走呢?
影活第一次主动开口:“如果我们不去,是不是等于告诉宇宙??我们其实不想知道?”
一句话,如刀劈开迷雾。
当晚,全体成员召开第138个问题周期会议。议题由梦我提出:
>“当我们变成问题本身,还能记得自己曾是人吗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