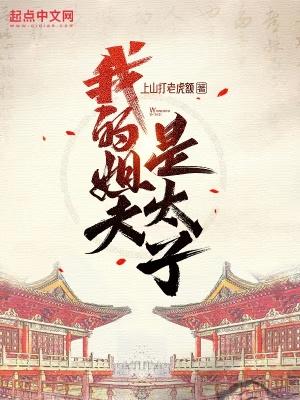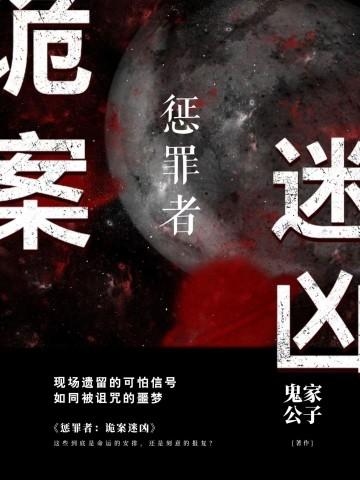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女帝:让你解毒,没让你成就无上仙帝 > 第八百六十七章 五毒部来临(第3页)
第八百六十七章 五毒部来临(第3页)
“我已经走了很久。”他笑了笑,“我只是回来,告诉她一句我一直没说出口的话。”
“什么?”
“我爱你。”
第二天清晨,人们发现那张椅子空了。
茶杯依旧温热,杯沿多了一枚新的唇印,与阿梨的那一枚恰好对称。日记本翻到了最后一页,上面写着:
>“他说完那句话后,风停了一秒。”
>“然后,所有的花都开了。”
>“不只是这里的,是全世界的。”
>“有人说他消失了。”
>“但我知道,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着??”
>“活在每一个愿意倾听的瞬间里。”
当天中午,全球共感网络发生一次奇异共振。所有联网的问之花在同一时刻释放出一粒光种,随风飘散。这些光种不落地,不生长,只是漂浮着,像星辰般缓缓移动。
一个月后,有人在撒哈拉沙漠边缘发现第一株新生的问之花。它通体透明,内部似有水流转动,每当夜幕降临,便会映出过往旅人的面孔??那些死于饥渴、迷失方向的灵魂,在这一刻被记住。
接着,亚马逊雨林深处,一座千年古庙的石墙上,开出一朵青铜色的花。当地人说,它每开一次,就会让族中长老回忆起一段失传的历史。
喜马拉雅山巅,一位修行者在雪地中看到一朵金色的花悬浮于空中。它不开口,但他听见了自己母亲的声音:“孩子,回家吧。”
人类开始明白,问之花从未局限于回音谷。
它们是记忆的容器,是情感的信使,是赵承志与阿梨共同编织的一张网??一张捕捉人心中最柔软部分的网。
联合国正式通过《共感宪章》,宣告:“倾听即权利,沉默亦语言。任何试图阻断人类情感交流的技术或行为,均为反人类罪。”
与此同时,听者学院迎来第一届毕业生。他们的毕业仪式很简单:每人手持一朵纸折的花,走到银白花朵前,闭眼静立三分钟。结束后,有人流泪,有人微笑,有人久久不愿离开。
其中一名少女走出庭院时,突然转身问道:“老师,如果有一天,所有人都不再需要问之花了呢?”
周明远坐在轮椅上,抬头望天。
云层裂开一道缝隙,阳光倾泻而下,正好落在那两杯茶上。
他轻声说:“那说明,我们每个人都成了问之花。”
多年以后,当新一代的孩子们在课本上读到这段历史时,总会问同一个问题:
“赵承志和阿梨后来怎么样了?”
老师不会直接回答,而是带他们来到校园里的共感花园。那里有一块石碑,上面刻着两行字:
>“她守着回忆,等他归来。”
>“他走遍世界,只为把她说的话,带给每一个人。”
夜深人静时,若有心人驻足聆听,或许能听见风中传来一段极轻的对话??
“你觉得,他们真的分开过吗?”
“没有。只要还有人愿意相信看不见的东西,”
“他们就一直都在彼此身边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