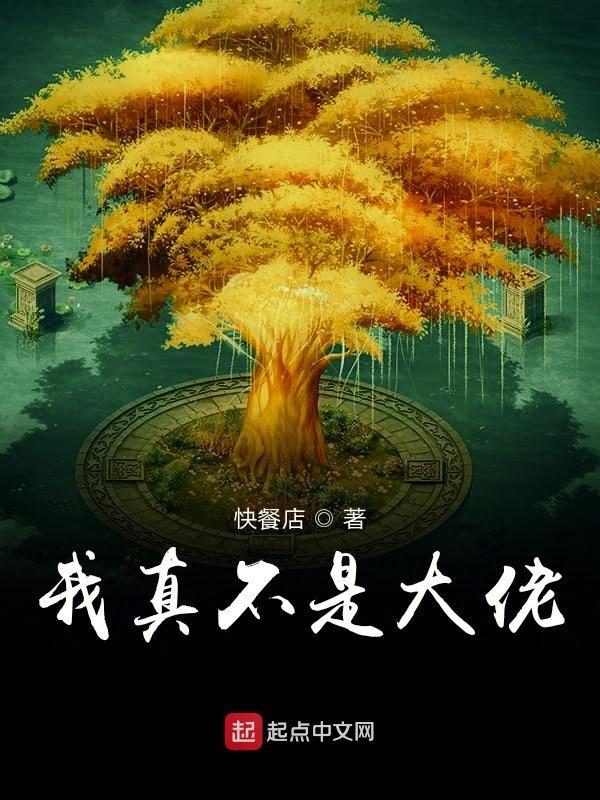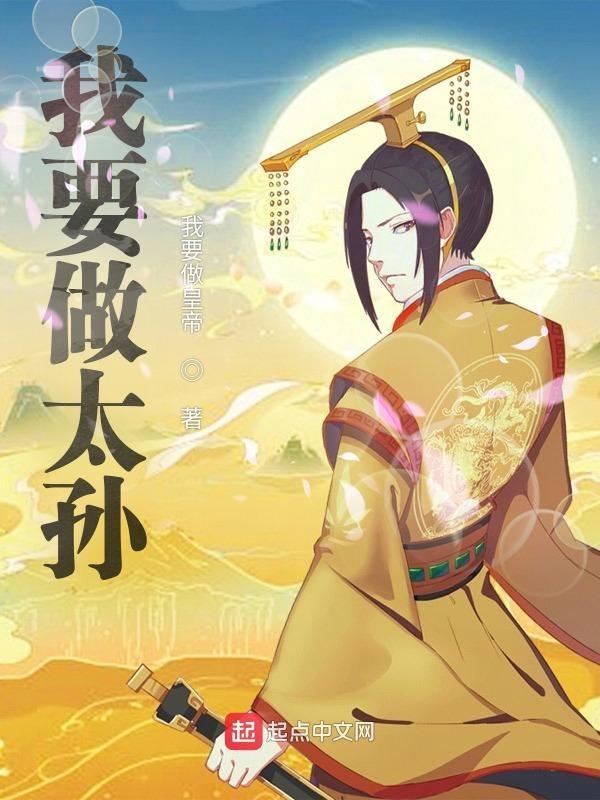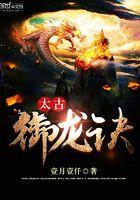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带着古人穿回现代 > 番外篇 灶王爷的新灶与旧火(第1页)
番外篇 灶王爷的新灶与旧火(第1页)
京郊半山别墅的厨房,晨光正好。巨大的落地窗外,庭院里谢镇山指挥“铁牛”与小虎子“征战”的嬉闹声隐隐传来,衬得厨房里愈发宁静。柳氏去了日内瓦的慈善会议,偌大的空间里,只有灶台上细微的咕嘟声,以及食物在热力作用下悄然变化的、近乎无声的细语。
老夫人站在宽大的岛台前。一身质地极佳的深紫色香云纱改良褂子,衬得银发愈发如雪。她没戴老花镜,那双阅尽千帆、曾让米其林大厨都汗颜的眼睛,此刻正锐利如鹰隥,紧紧盯着岛台中央一个造型简洁流畅、泛着哑光金属光泽的方盒子——谢砚秋新送来的“分子料理智能烹饪中心”,据说是德国最新款,能精准控温、真空慢煮、低温料理,集万千科技于一身。
“分子料理?”老夫人从鼻子里哼出一声,带着金玉堂老掌柜点评新学徒手艺般的挑剔,“花里胡哨!老祖宗传下来的火候二字,岂是几个铁疙瘩能算明白的?”
话虽如此,她那布满岁月沟壑却异常稳定的手,却已经拿起了附赠的、厚得像砖头的中文说明书。指尖划过光滑的铜版纸,发出轻微的沙沙声。她看得极慢,眉头微锁,仿佛在研读一本失传的武功秘籍。偶尔,她伸出食指,在空气中虚点一下某个复杂的图标,又或是无意识地模仿着旋钮转动的动作,嘴里念念有词:“…真空锁鲜…65度恒温…水浴…哼,说穿了,不就是个精细点的…煨罐子?”
她手腕上那条来自内罗毕基贝拉的彩色塑料小项链,在晨光下跳跃着朴拙的生命力,与眼前冰冷精密的仪器形成奇异的对照。
今天,她要复刻一道失传的点心——雪莲酥。并非食谱上记载的那种,而是她幼时在金陵娘家,伺候过前清御膳房老点心的祖母,凭记忆口述的方子。用料极简:上等澄面、精炼猪油、窖藏三年的玫瑰酱露、以及一味早已绝迹的野生高山雪莲子研磨的细粉(她用了最接近的莲子芯粉替代)。难点在于火候与手法的极致融合:油酥需用掌心温度缓缓揉开,与澄面皮结合时,力道的轻重缓急直接决定了酥层能否如雪片般千层绽放;烘烤时,炉温需先文后武,差一分则酥皮僵死,多一分则馅心焦苦。
这活儿,讲究的就是一个“心手合一”,一个“火眼金睛”。老夫人原本打算用她惯用的老式风炉,凭经验驾驭那跳跃的火焰。可偏偏,昨晚小虎子缠着她讲非洲故事时,指着她腕上的塑料项链问:“曾祖母,这个好看!比爸爸的智能手表好看!它能做饭吗?”孩子天真的话语,像一颗小石子投入心湖。她忽然就想试试,这号称能“精准复刻大师手法”的铁疙瘩,到底有几分斤两。
“滴——”智能烹饪中心发出一声悦耳的提示音,预热完成。幽蓝的屏幕亮起,选项繁多。
老夫人深吸一口气,如同即将踏入未知战阵的老帅。她按照说明书,小心翼翼地将揉好的、裹着玫瑰雪莲馅的生胚放入机器的真空密封盒,选择“低温慢煮酥皮”模式,温度设定65℃,时间…她犹豫了一下,凭感觉输入了45分钟。机器无声地开始工作,内部隐约传来水流循环的细微声响。
等待的时间漫长。老夫人背着手,在宽敞的厨房里踱步。目光扫过角落里那口被她盘得油光发亮的老铁锅,锅底还残留着昨夜煎饺的焦香;扫过墙上挂着的一排大小不一、木柄温润的桑刀;最后,落在岛台上那本摊开的、纸张泛黄、用蝇头小楷手写的《随园食单》残页上。那是她的根,她的魂。
45分钟到。机器“嘀嘀”提示。老夫人戴上隔热手套,如临大敌般打开密封盒。一股带着奇异低温感的玫瑰甜香飘出。里面的雪莲酥生胚…形态完好,表皮甚至带着一种低温赋予的、近乎半透明的润泽感,漂亮得像艺术品。
“看着…倒有几分意思。”老夫人眼中闪过一丝讶异,随即又绷紧了脸。她将生胚转移到机器的烘烤模块,按照提示设定了分段温度:先150℃定型10分钟,再升至180℃上色5分钟。
机器再次开始工作,内部风扇转动,热流循环。
老夫人抱着手臂站在一旁,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观察窗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。第一个10分钟结束,酥皮微微鼓起,颜色几乎没变。升温至180℃,观察窗里,酥皮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膨胀、分层,淡淡的金黄色泽晕染开来…
“成了!”守在旁边的小唐助理(被谢砚秋派来“技术支援”兼“防止炸厨房”)忍不住小声欢呼。
就在此时!
老夫人眼神陡然一厉,如同发现猎物破绽的老鹰!她猛地抬手,完全无视还在运行的机器和设定的剩余时间,精准而迅猛地按下了那个硕大的红色“停止”键!
“滋——”加热瞬间停止,风扇还在惯性转动。
“老夫人!时间还没到!”小唐惊呼。
“闭嘴!”老夫人低喝一声,动作快得不像老人。她一把拉开滚烫的烘烤仓门(隔热手套都来不及戴全),戴着厚布袖套的手闪电般探入,用特制的长柄银夹,将一盘十二个雪莲酥迅疾无比地夹了出来!动作行云流水,带着一种千锤百炼的、与时间抢火候的决绝!
刚出炉的雪莲酥被放在提前备好的竹制凉架上,发出细微的“噼啪”轻响,那是极致酥脆的表征。一股难以形容的、融合了玫瑰清甜、莲子微苦回甘、以及猪油与高温激发的、直抵灵魂的酥香,如同炸弹般在厨房里轰然爆开!瞬间盖过了机器残留的、带着金属味的热风。
再看那酥:层!千真万确的千层!薄如蝉翼,洁白如雪,层层叠叠,蓬松轻盈,仿佛轻轻一碰就会化作漫天飞雪。顶端因高温而晕染开的焦糖色斑点,如同雪地上落下的几点暖阳,恰到好处。
老夫人凑近,鼻翼微微翕动,捕捉着那稍纵即逝的巅峰香气。然后,她拿起旁边一把锋利的小银刀,手腕稳如磐石,对着其中一个雪莲酥,轻轻一划。
“嚓——”一声极其轻微却无比悦耳的脆响。酥皮应声而开,断面整齐,层次分明如万卷书页!内里深琥珀色的玫瑰雪莲馅心,如同熔化的宝石,缓缓流出,浓郁的甜香中带着一丝高山雪莲特有的清冽微苦,完美地平衡了油腻。
小唐看得目瞪口呆,口水差点流出来。
老夫人却眉头微蹙,用指尖沾了一点馅心,送入唇间细细品咂。半晌,才缓缓道:“火候…还差一分。这机器,升得太急。最后那三十秒的猛火,它算不准。馅心里的那点‘高山雪意’,被压住了三分。”她指了指酥皮顶端那完美的焦糖斑点,“这‘金顶’,靠的是眼疾手快,抢的就是那一刹那的火头!机器?它懂什么叫‘刹那’?”
她拿起另一个雪莲酥,走到窗边。窗外,谢镇山正得意洋洋地向小虎子展示他如何“驯服”了“铁牛”。老夫人看着,嘴角勾起一丝几不可察的、带着了然与傲然的弧度。她低头,看着手中这枚凝聚了科技与匠心、却仍被她挑出“一分”不足的雪莲酥,又轻轻抚过腕间那条色彩斑斓的塑料项链。
冰冷的机器,能复制温度,能计算时间,甚至能模拟某种程度的“稳定”。但舌尖上那稍纵即逝的巅峰之味,灶膛前那与食材共呼吸、与火候共舞的“刹那”灵犀,还有这粗糙项链背后,那个小女孩清澈眼睛里的期盼…这些,是算法永远无法穷尽的“混沌”,是人心才能捕捉的“真味”。
她拿起智能烹饪中心的遥控器,没有关机,而是调出了“自定义程序”界面。布满皱纹却异常灵活的手指在屏幕上快速点按、滑动,将刚才记录下的低温慢煮时间、她手动中断的烘烤温度和时间点,以及她品评后对馅心温度的微调建议,一一输入。
“小唐,”老夫人头也不抬地吩咐,声音恢复了平日的沉稳,“记下:下次做‘雪莲酥’,先用这铁疙瘩的低温稳住酥皮筋骨,省点揉面的力气。最后那‘金顶’和馅心的火候…还得靠这个。”她指了指自己的眼睛,又拍了拍心口的位置。
“是!老夫人!”小唐赶紧应下,看向那台昂贵机器的眼神,仿佛在看一件刚刚被“开光”的法器。
老夫人将输入完程序的遥控器随手放在一边。她走到那盘凉得恰到好处的雪莲酥前,用银夹小心地夹起一个,放在掌心大小的甜白釉瓷碟里。然后,她端着碟子,步履沉稳地走出厨房,走向庭院里那一老一小。
晨光洒在她银白的发丝和深紫色的衣袂上,也照亮了她手中那枚宛如艺术品的酥点。新灶与旧火,算法与灵犀,冰冷机器与温热人心,都在这一刻,在她布满岁月却依旧明亮的眼眸里,达成了某种微妙而坚实的和解。
“镇山,小虎子,”她清朗的声音在晨风中响起,“过来。尝尝曾祖母的‘新式’雪莲酥。看看这‘铁疙瘩’的筋骨,配上老手艺的魂儿…是个什么滋味。”
阳光落在酥皮顶端那完美的焦糖斑点上,金灿灿的,如同灶王爷新收的供奉,也像旧时光里,从未熄灭的火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