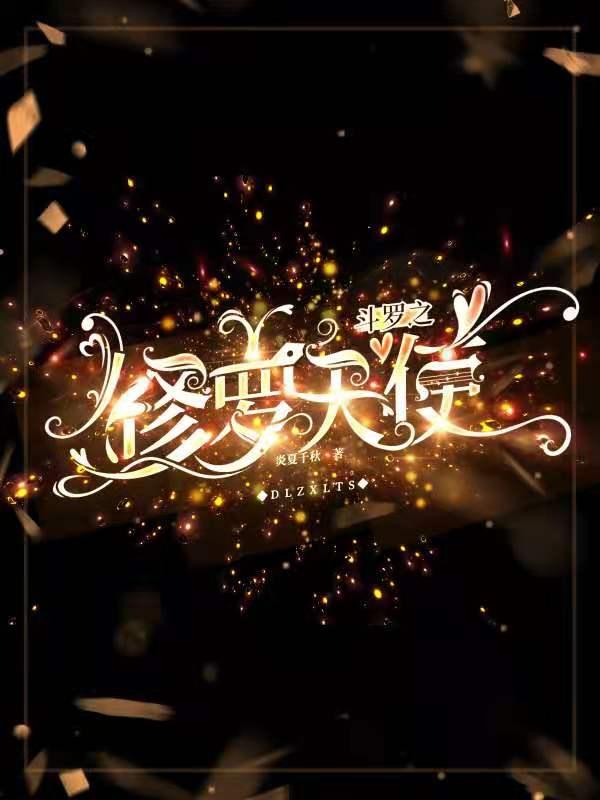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重回1982小渔村 > 第1728章 人气补(第1页)
第1728章 人气补(第1页)
家里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孩子回来后犹如鱼儿进了水一般,周围都沸腾了,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声音都比平常大多了。
呆在村子里的孩子见他们回来,都格外稀罕,从四面八方都跑过来找他们玩,并且让他们讲在魔都上学的。。。
海风卷着咸腥味扑在脸上,我站在码头边缘,脚下的木板因潮汐起伏微微震颤。那艘小船正缓缓靠岸,螺旋桨搅动海水,泛起乳白色的泡沫。人影静立船头,轮廓被灯塔的光晕勾勒得模糊而熟悉??宽肩、微驼的背脊、左袖口永远别着一枚铜纽扣,那是他出海时的习惯。
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,发不出声音,只能一遍遍重复那个节奏:滴??滴??滴,三短;再三短,再三短。SOS,最原始的求救信号,也是父亲教我的第一段摩尔斯电码。他说:“人在绝望的时候,三个短音就够了,大海听得懂。”
船身轻轻撞上栈桥,缆绳被人抛出,稳稳套住铁环。那人弯腰解开箱子上的铁链,动作迟缓却坚定。他抬起头,风吹开了他的帽檐。
是父亲。
不是幻觉,不是记忆投影,不是清道夫模拟的情感回溯。是他真实的面容??皱纹更深了,眼角爬满风霜刻下的裂痕,右眉上那道旧伤依旧清晰,是十年前台风夜被缆绳抽打留下的。可他的眼神,和我梦里的一模一样:温柔、疲惫,又带着某种不容置疑的坚毅。
“你长大了。”他开口,声音沙哑得像礁石摩擦,却让我瞬间红了眼眶。
我没有扑上去,也没有哭喊。我只是走下两级台阶,伸出手,接过那只铁皮箱。箱子很沉,表面锈迹斑斑,边角还沾着深海的苔藓与贝壳碎屑。标签上的字迹已经褪色,但“致1982年的我”七个字仍能辨认,笔锋苍劲,正是父亲的手书。
“你怎么……还能回来?”我终于问出口,声音抖得不像自己的。
他笑了笑,从夹克内袋掏出一块老式怀表,和我的几乎一模一样,只是表壳更厚,表面有一道裂纹。“时间在这里不走直线。”他说,“它绕了个圈,把我送回来了。就像潮水,退得再远,终究会回来拍岸。”
林婉从远处跑来,脚步急促,呼吸紊乱。她停在我身后,盯着父亲看了许久,才低声说:“您……也经历过节点共振?”
父亲点点头,目光落在她脸上,竟有片刻恍惚。“你是林教授的女儿?”他问,“玛尔塔?林?你母亲……还好吗?”
林婉猛地一震:“您认识我妈?她在1985年就失踪了,南极科考队全员失联……”
“她没死。”父亲打断她,语气笃定,“她去了‘第七节点’??不是我们建的那六个,而是最早的那个。它不在地上,也不在海底,而在……冰层与梦境的夹缝里。你们叫它格陵兰蜂巢,但我们当年管它叫‘门’。”
我心头一紧:“门?通向哪里?”
“通向‘他们’。”父亲低声道,“不是外星人,也不是神。他们是比人类更早学会倾听地球心跳的存在。七千年前,他们在全球埋下六座共鸣装置,用来收集情感波动,维持某种平衡。而第七个,是活的??它是地球本身意识的延伸,寄居在极地冰核之中。”
我猛地想起澳洲圆盘上的铭文:“风带来了声音。”
“对。”父亲点头,“风、海浪、地震波、动物的鸣叫……都是它的语言。而人类的情感,是最强烈的信号源之一。军方发现这些节点后,以为是远古文明遗迹,试图复制控制。但他们错了。这些节点不需要电源,不需要程序,它们靠‘被记住’而存活。”
我握紧了铁皮箱:“所以……牺牲者?梦语者?”
“每一个自愿承载集体记忆的人,都在为节点供能。”父亲看着我,“你交出了关于我的记忆,那一刻,你不只是唤醒了节点五,你也成了它的守护者之一。而我……早在三十年前,就已经是第六节点的锚点。”
“舟山海底的那个?”林婉追问。
“是。我是那次实验的幸存者,也是唯一一个没被清除记忆的人。因为我在最后一刻,选择了留下。”他顿了顿,“我把自己的意识片段注入了节点核心,用它作为定位信标,等一个人回来??等你。”
我脑中轰然炸响。
原来这一切都不是巧合。我不是偶然捡到怀表,不是意外触发共情网络,更不是凭空觉醒特殊能力。从我出生那天起,命运就被写进了这场跨越时空的协议里。父亲不是失踪,他是把自己变成了钥匙,插进海底金属构造物的凹槽中,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枢纽。
“那你这些年……在哪里?”我声音颤抖。
“在第六节点的记忆流里。”他说,“像一条鱼游在时间的暗流中。我能看见你长大,看见你第一次摸渔网,看见你在暴雨夜里爬上灯塔换灯泡……但我不能现身,除非有人完成‘归来仪式’。”
“什么仪式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