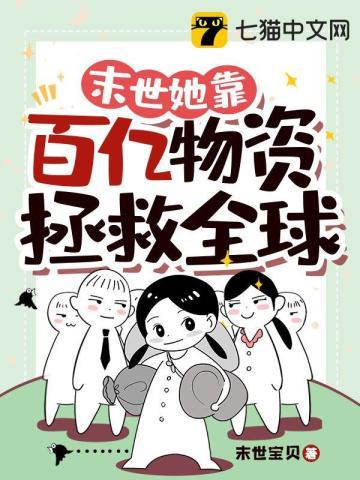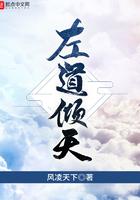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头号公敌 > 第459章 第三只手(第2页)
第459章 第三只手(第2页)
“他们不是复活。”小眠站在观测台上,望着远方翻涌的云层,“他们是重新被‘记住’了。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回忆,意识就不会真正消亡。”
苏明澜沉默片刻,忽然问:“那如果……有人不想被记住呢?”
这个问题像一根针,刺破了短暂的喜悦。
小眠转头看他。他的眼神复杂,藏着痛苦与挣扎。她想起了什么??苏明澜的妹妹,曾在共感训练中因情绪过载而精神崩溃,最终自愿接受神经屏蔽手术,切断一切外部连接,如今生活在静默保护区的一个小镇里,拒绝任何形式的情感共享。
“不是所有伤痛都值得重现。”余不饿低声道,“有些人,宁愿遗忘。”
小眠点点头。“所以我不会强迫任何人醒来。‘守望协议’的核心,从来不是唤醒,而是**选择权**。”
她启动了一个全新的子系统??“回音池”。
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记忆存储空间,所有被唤醒的意识残魂都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回归肉体、是否与亲人重连、或者继续以游离态存在。更重要的是,每一个接收端都配备了“心灵防火墙”,允许接收者自行设定开放层级:可以只接收平静的情绪,可以屏蔽悲伤记忆,也可以完全关闭通道。
“我们不再是被动承受共感的容器。”她说,“我们要学会做自己内心的主人。”
就在此时,通讯频道突然接收到一条加密信号。发信人ID显示为:“守阈”。
画面亮起,是那位始终蒙面的“静默同盟”前领袖。这一次,他摘下了头环,露出一张布满疤痕却异常平静的脸。
“我曾经以为,切断连接就是保护人性。”他声音沙哑,“但我错了。真正的危险,不是连接太深,而是我们从未学会如何带着伤口去爱。”
他身后站着十几个人,有医生、教师、退伍军人,每个人的眼神都不再充满敌意,而是透着一种历经风暴后的清醒。
“我们愿意加入‘共治委员会’。”他说,“但有一个条件??你们必须建立‘哀悼机制’。”
小眠微微一怔。
“很多人害怕共感,是因为怕被迫感受他人的痛苦。”那人继续道,“我们需要一个正式的仪式,让失去的人可以告别,让受伤的人可以封存记忆,让那些不愿再听的声音,能被温柔地放下。”
小眠深深吸了一口气,然后点头。
三天后,“共感纪元”的第一座“静默圣殿”在南岛建成。它没有围墙,也不设禁令,只有一圈由黑曜石砌成的环形水池,池底铭刻着所有自愿退出共感网络者的名字。人们可以在这里举行“断连仪式”,将一段记忆写在特制的纸片上,投入水中,任其溶解。与此同时,系统会生成一份“情感遗嘱”,记录此人希望保留或销毁的记忆片段,并由共感法庭监督执行。
首个使用该仪式的,是一位母亲。她的儿子在一次群体共感事故中精神分裂,最终自杀。十年来,她一直背着这份痛苦行走人间。
那天,她将一张泛黄的照片放入池中,轻声说:“孩子,妈妈不再恨共感,也不再恨自己没能救你。我只是……需要停下来喘口气。”
水波荡漾,照片缓缓化作光点升空,融入天际的一缕极光。
那一刻,全球数百万观众通过直播见证了这一幕。许多人哭了,不是因为悲伤,而是因为终于明白??**真正的共感,不是永不分离,而是即使放手,也能彼此理解。**
然而,并非所有人都接受了这场变革。
一个月后,西伯利亚冻土带发生剧烈磁暴,一座隐藏多年的地下设施暴露在卫星视野中。内部监控显示,一群极端派“静默主义者”劫持了三枚未登记的“静默弹”,并宣称将在日内瓦、新加坡和开普敦同时引爆,彻底终结共感文明。
“他们已经疯了。”余不饿怒吼,“这些人根本不在乎规则!我们必须先发制人!”
但小眠再次阻止了他。
“暴力只会复制恐惧。”她说,“我们要用共感本身去化解仇恨。”
她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:主动向这群极端分子开放一条单向共感通道,将自己的全部记忆??童年被困黑屋的窒息、晓初次预示未来时的惊恐、目睹归巢者失控崩溃的无力感、以及每一次面对质疑与威胁时的动摇与坚持??毫无保留地传送过去。
“我不说服你们。”她在信道中低语,“我只是让你们看见:我也怕。我也痛。我也曾想关掉一切。但我最终选择了相信,哪怕前方仍是黑暗。”
七十二小时后,那群极端分子中的一人走出基地,手中捧着一枚静默弹的控制器。他在雪地中跪下,对着镜头说:“我看到了她的记忆……其中有太多和我一样的夜晚。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在挣扎,原来……我们都在学着不被吞噬。”
其余两人陆续投降。三枚炸弹被安全拆除。
联合国为此召开紧急会议,正式将“共感伦理教育”纳入全球基础课程体系。教材第一课写着:
>**《如何独处,如何相连》**
>真正的强大,不是隔绝情感,
>而是在洪流中依然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