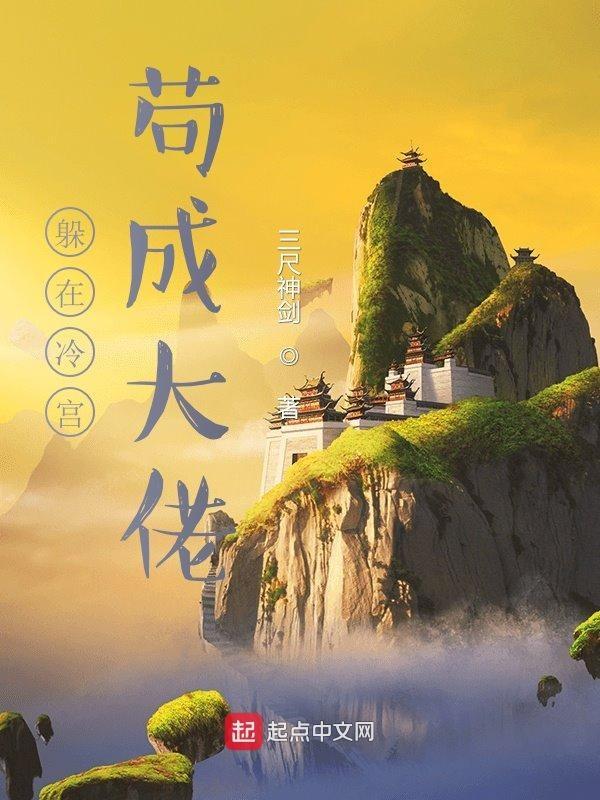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我本将心向沟渠 > 幻灭(第1页)
幻灭(第1页)
酒香丝丝缕缕漫过佳人罗裙,绕上玉颈轻触桃腮,惹得那抹胭脂红晕漾开一串银铃娇笑,在耳畔堆出三尺温云。
主座的男人带着点殷勤的笑,小心翼翼地开了口:“贤侄瞧着,府上这些小玩意儿,可还……勉强能入眼?”
一语未了,却听“轰——”一声,门从外面被大力推开。
祁悠然立在门口,与满室浮华格格不入:“国公爷真是热心肠,这么火急火燎地往侯府塞人。”
庆国公皱眉,下意识地便去觑顾濯的脸色。
只见那位新晋的永安侯爷,一个人冷冷清清坐在那,神色依然淡漠。他并未抬眼,浓密的眼睫低垂,遮住了深潭般的眸子,只露出线条冷硬的下颌。
庆国公心头一松,想起京中那些沸沸扬扬的流言,什么夫妻离心、郡主失势。他自觉揣摩透了七八分,那点虚浮的底气便涨了起来,腰杆也硬了几分。
“郡主此言差矣!”他捋了捋胡须,带着点长辈训诫晚辈的倨傲腔调,“自古贤德妇人,当以夫家子嗣为重。这三妻四妾,乃是天经地义。郡主身份尊贵,更该是女中典范,何至于这般如临大敌的模样?”
他顿了顿,扫过祁悠然愈发难看的脸,眼神里不由得掺着一丝轻蔑,又补了一句:“况且,您这般不管不顾地闯进来,可有半分大家闺秀、后宅主母该有的模样?”
祁悠然却是笑了,嘴角弯起一个讽刺的弧度,轻飘飘地提醒:“国公爷,上一个这般想着规训我的,三年前死在了天牢里。”
“哦,对了,他也姓林。”祁悠然顿了顿,“说不定早八百年前,你们还是本家呢。”
当年林枫眠在官场如日中天,这位可没少借着同姓的由头去攀附巴结。
然而,便是林枫眠,也从未说出这般关于“贤德”的混账话来,他又算个什么东西!
“你!”庆国公喉头猛地一哽,气得胡子乱颤,脸色由红转青,指着祁悠然的手指抖得厉害,“你这个……”
“公爷。”微凉的声音在屋内响起,不高,却打断了那怒不可遏的恶言。
顾濯终于抬了眼皮:“陛下前日还特意问起令孙在工部的差事,言及行宫修缮,劳苦功高。”
庆国公一愣,府里这些年在工部见不得光的勾当不少,也正是因为害怕新皇清算,他才腆着张脸宴请顾濯。
原指望能从他嘴里探出点蛛丝马迹的风声,好给自己寻条退路,不料顾濯却是滴水不漏。
眼下他主动提及,是不是在释放可以拉拢的信号?
况且,这对夫妻……京里传得再难听,什么“离心离德”、“怨偶成仇”,可眼下不还在一处么?面上到底不好撕破脸得罪死了。
这么一想,他脸色缓了缓,刚想顺着那点微弱的信号再试探几句,顾濯却已起身。
“夜深了,晚辈就不打扰公爷雅兴了。”
顾濯的目光重新落回祁悠然身上,平静得近乎漠然:“走吧。”
。
回府的马车上,空气滞涩。
“你不该来的。”顾濯不赞同地蹙眉。
“江烨说你公务缠身,日理万机,原来忙的,便是这个?”祁悠然反问。
“你不需要担心什么,我自会尽到一个丈夫的本分。”顾濯冷冷看着她,语气疏离。
祁悠然像是听到了极有趣的笑话,逸出一串阴阳怪气的轻笑。
“哦?本分?”她身体微微前倾,不甘示弱地呛道:“也包括,同房吗?”
“……”顾濯的身体僵了一瞬,没有说话。
“夫君可是要续上先前在城南别院的那一晚?”
“……”顾濯喉结几不可察地滑动了一下,依旧回以沉默。
祁悠然不耐烦地抬手揉了揉眉心。
动作间,茜色的袖口滑落一截,露出一段雪白的手腕,在昏昧的光线里,像沥水的玉。
。
城南别院。
彼时顾濯被人下了药。
她收到消息匆匆赶到时,竟撞见向来端方自持的人,一副几乎撑不住的模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