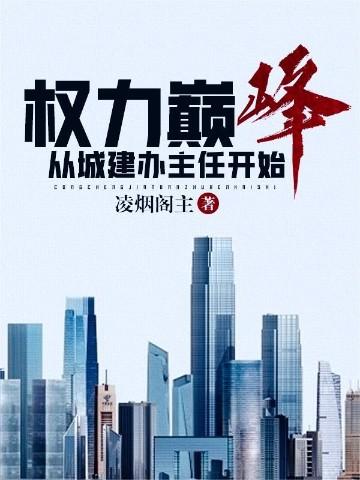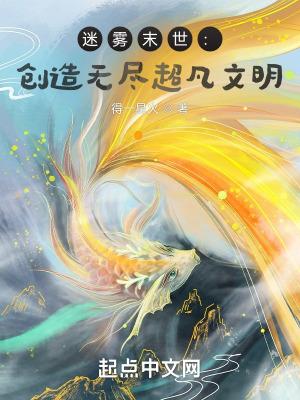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虎贲郎 > 第706章 荆益之别(第1页)
第706章 荆益之别(第1页)
襄阳城内,镇南将军府。
幕府主簿蒯良与从事北地人傅巽肩并肩行走在走廊内。
两人步伐悠闲、散漫,不紧不慢。
蒯良双手捧着一叠纸张……北方因为战乱,纸张早已成为奢侈品。
也就这两年。。。
雪落无声,覆了三日三夜,将北方的荒原裹进一片素白。守约书院的屋檐垂着冰棱,如剑悬空,映着晨光微寒。院中石碑新刻一行字:“柏枝不死”,笔锋刚劲,是卫觊亲书。十年光阴如刀刻石,深痕入骨,不单在碑上,更在人心。
柳氏立于碑前,手中捧着一卷泛黄竹简,指尖抚过那些被血与火浸透的名字??张五郎、陈十三、王破虏、薛怀山……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断肠往事,一场无人祭拜的葬礼。如今这些名字被郑重录于《信义录》,每年春祭时由孩童齐声诵读,声震太学宫墙。
她转身望向廊下那株老柏树,枝干虬曲,半边焦黑,那是十年前晋阳大火中救回的残株,移植至此。有人说它活不过冬,可它偏偏抽了新芽,嫩绿如初生之眼,睁看着这人间沉浮。
“它比我们倔。”裴元昭拄杖走来,胡须已染霜色,左臂袖管空荡??那一战断于汾水桥头,为掩护费榕撤退,他独战七骑,终以残躯劈开生路。
柳氏点头:“就像卫觊说的,有些东西,烧得只剩灰,风一吹,反倒散得更远。”
裴元昭低笑:“他倒是越来越像个夫子了,整日讲‘心火’‘誓约’,可我知道,他夜里还练刀,一刀未停。”
话音未落,陈七郎自门外蹒跚而入,背驼得厉害,拐杖敲地声沉重如鼓点。他抬头看了看柏树,又看向两人,嗓音沙哑:“昨夜我又梦见雁门了。五百人站在雪坡上,没人说话,就那么看着我。他们等了十年,不是为了听书生念名字,是为了有人替他们问一句:为什么?”
柳氏默然。
裴元昭叹道:“可天下太平了。朝廷废了影弃,设了守约司,连赵氏宗庙都被削籍除名。你说的‘为什么’,难道还不够答案?”
“太平?”陈七郎冷笑,“不过是换了枷锁罢了。你们以为废了一个机构,就能斩断野心?我听说洛阳最近在重修太庙地基,挖出三十七具尸骨,全穿着虎卫旧甲,手脚反绑,颅骨有钉孔??那是当年被活埋的逃兵家属。可圣旨怎么说?‘前朝乱党,罪有应得’。谁定的罪?谁下的令?没人问。”
空气骤冷。
良久,柳氏轻声道:“所以你怀疑,赵太师虽死,他的根还在?”
“根没断。”陈七郎盯着她,“只是换了个地方长。从前藏在阳符名录里,现在藏在律法条文中;从前靠血统杀人,现在靠官文杀人。手段变了,目的没变??还是要把真相压进土里。”
三人沉默对坐,炉火噼啪作响。
忽有脚步声急促而来,孙九斤推门而入,披风上积雪未融,眉梢凝冰。“出事了。”他喘息未定,“北境快马传讯:朔州守将突然封锁边境,扣押所有携带铜符者,称发现‘逆党余孽结社图谋复辟’。已有十二名守约塾先生被捕,其中三人……是当年虎卫遗孤。”
裴元昭霍然起身:“凭什么叫他们逆党?他们连刀都没碰过!”
“因为他们在教孩子认祖谱。”孙九斤冷冷道,“认的是真正的祖谱,不是朝廷钦定的那一套。他们教孩子们知道,自己的祖父曾为国战死,却被诬为叛贼。这一条,触了忌讳。”
柳氏猛地站起,手按腰间匕首:“我们要去。”
“不能去。”一个声音从门口传来。
卫觊缓步而入,身上仍是一袭旧布衣,却挺拔如松。十年讲学未改其骨,反添几分沉静锋芒。他手中握着一封密函,封口烙着一只无面人形印??那是“守约司”最高机密文书的标记。
“这不是武力能解的局。”他说,“朝廷这次动手,不是冲动,是试探。他们在看,我们会不会跳出来救人。一旦我们动了,就会被定性为‘聚众抗命’,正中下怀。”
“那你让他们白死?”柳氏怒视他,“你还记得费榕临终前说什么吗?‘别让故事停在我们这一代’!现在故事还没传出去,就被掐住了喉咙!”
卫觊直视她双眼,一字一顿:“所以我打算进京。”
众人一怔。
裴元昭皱眉:“你疯了?上次入宫讲学,多少双眼睛盯着你?你那句‘宁为碎玉,不作完奴’至今被人参奏为‘煽动民变’!你现在回去,等于送上门!”
“正因如此,我才必须去。”卫觊将密函置于案上,“守约司内部有人递信给我,说此次清洗背后,有一份新的《阳符名录》正在编纂,名为《正统源流》,要将七脉血脉重新归一,奉一人为主,其余皆贬为‘旁支伪嗣’。而这名单的执笔者……是当朝太子少傅,李玄度。”
“李玄度?”陈七郎瞳孔骤缩,“他是……影弃最后一任副使!”
“没错。”卫觊声音低沉,“他本该随赵太师一同伏诛,却因及时倒戈,反而升官晋爵。这些年他表面支持改革,暗中却一直在搜集阳符残卷,重建符系体系。他不信誓言,只信控制。他要的不是一个守约的世界,而是一个由他定义‘正统’的世界。”
屋内寂静如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