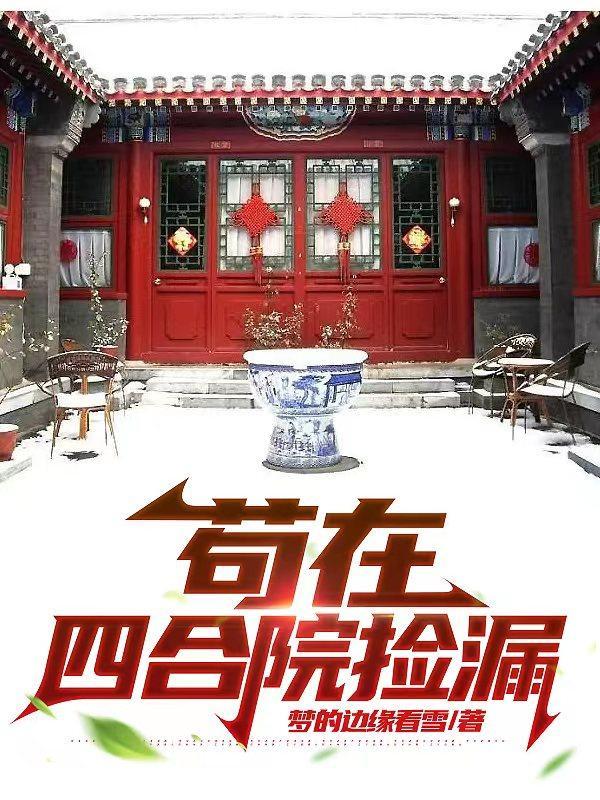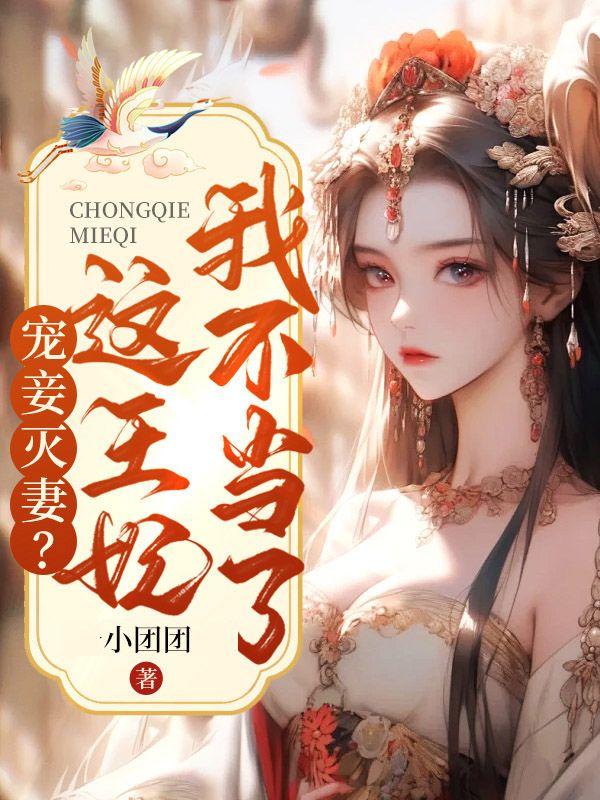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哥布林重度依赖 > 第335章 谨慎补刀与轻松治疗(第4页)
第335章 谨慎补刀与轻松治疗(第4页)
>“你问过我们,是否等了很久。”
>“现在我们可以回答:是的。”
>“但我们等的,从来不是你恢复记忆。”
>“我们等的是,你终于愿意承认??你一直是我们的一部分。”
>“叙述者不死,因为他们活在每一次被复述的瞬间。”
>“而你,不必记得一切,只需继续相信:有人会接着讲下去。”
光柱渐渐收敛,岩柱恢复平静。唯有那支笔,缓缓从石缝中升起,漂浮至半空,笔尖朝下,静静悬停,仿佛在等待下一任执笔者伸出手。
我没有去接。
而是退后一步,转身看向身后的五人。
“谁想试试?”我问。
短暂的沉默后,小女孩上前一步,伸出稚嫩的手。
笔轻轻落入她掌心。
那一刻,整片冰原响起千万种声音??是风、是雪、是心跳、是呼吸,是所有曾经沉默的生命共同谱写的序曲。
她握紧笔,在空中划下第一道痕迹。
没有文字,没有语言,只有一个圆圈。
但她笑了。
我知道,那是一个句号,也是一个开端。
我们原路返回。
归途中,我发现自己的记忆并未恢复,也没有更多“真相”浮现。但我已不再追问。因为真正的记忆,本就不该只存在于脑海中,而应流淌在世界的脉络里。
半年后,我在村庄外新建的图书馆担任顾问。这座馆没有管理员,书籍也不编号。任何人想借阅,只需留下一段自己的故事作为“押金”。有个孩子借走《哥布林冶炼技艺》时,留下了一幅画:一只小手牵着大手,走在星光下。
我把它挂在墙上。
某日清晨,邮差送来一封匿名信,里面只有一张照片??是“终笔之柱”附近的新景象:那株语言之树的幼苗已然长成,枝叶繁茂,果实累累。每一颗果子里,都藏着一个正在孵化的故事。
背面写着一行小字:
>“你说你不记得了。”
>“可我们都记得你。”
>“所以,请继续走下去吧??哪怕只是作为一个听众。”
我收起信,走出门外。
春雪初融,溪水潺潺,岸边有几个孩童蹲着,用树枝在湿泥上写字。
一个男孩抬头问我:“老爷爷,怎么才算一个好的故事?”
我想了想,笑着说:
“当你写完最后一个字,却觉得它才刚刚开始的时候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