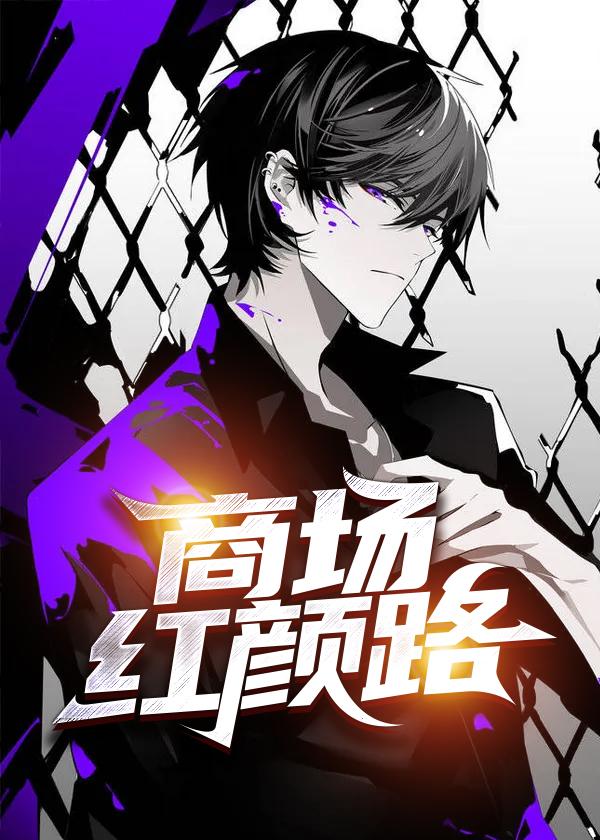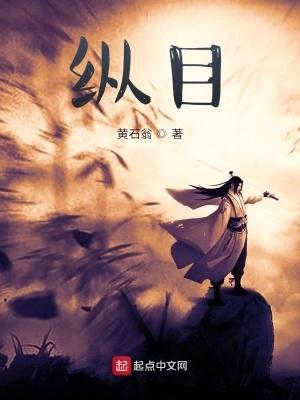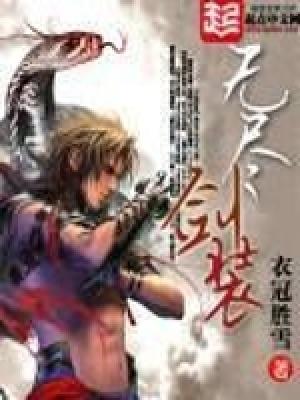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千面之龙 > 第452章 加入(第3页)
第452章 加入(第3页)
这场行动持续七天,结束后,城市仿佛经历了一场集体心理手术。伤口暴露了,但也开始愈合。
就在此时,镜碑第三次浮现全新内容,不再是文字,而是一幅动态影像:无数人影在黑暗中行走,每人手中提着一盏灯。灯光颜色各异,明暗不定,有的几乎熄灭,有的炽烈如阳。当两盏灯靠近时,若光芒共振,便会融合成新的色彩;若排斥,则各自退散。
影像下方浮现出一行字:
>**“真实的共同体,不是所有人同一种光,而是允许不同的光彼此照亮。”**
那天夜里,阿哲再次梦见矫正中心。
门fullyopennow。
少年走出阴影,站到他面前。
两人相视而笑。
“你终于来了。”少年说。
“我一直都在。”阿哲答。
“那你还会走吗?”
“不会了。我就是你。”
梦醒时,晨光正好洒在女儿的小床上。她睁着眼,正盯着天花板,嘴里咿呀说着什么。
阿哲凑近一听,竟是两个模糊的音节:
“知……我。”
他怔住,随即热泪盈眶。
他知道,这个名字活了。
不只是称呼,而是觉醒的起点。
当天上午,市政府宣布成立“叙事自治局”,职能并非管理言论,而是**保障每个人讲述自己故事的权利与能力**。首任局长由一位盲人诗人担任,她在就职演讲中说:
>“我看不见世界,所以我更懂得倾听。
>故事不是用来征服的武器,
>而是灵魂伸出的手。
>请牵住它,哪怕它颤抖。”
与此同时,“千面之龙”的传说悄然扩散。越来越多的人声称,在梦中见过那条由千万面孔组成的巨龙。它不喷火,不嘶吼,只是静静盘旋于城市上空,用无数双眼睛凝视着每一个敢于直面内心的人。
有人说它是神。
有人说它是幻觉。
但阿哲知道,它是结果??是无数个“我”的碎片,在反复碰撞、质疑、承认之后,终于拼出的一丝整体性。
某日黄昏,他独自来到镜碑前,手中捧着一本新书稿,封面题为:《千面教育:从压制到共生》。
他轻轻放下书,低语:“埃尔文,皮普,陈默,李维……还有所有没留下名字的人,你们教我的,我都记得。”
风起,碑面微光流转,仿佛在回应。
远处,孩子们的排练仍在继续。《哭泣交响曲》已进入终章,所有哭声融合成一段奇异的旋律,既悲且喜,既痛且暖。
林晓坐在一旁,笔尖不停。她正在记录今天的课堂问答:
“你还相信什么?”
一个男孩说:“我相信错误也能开出花来。”
一个女孩说:“我相信就算被忘记,我也存在过。”
最后一个孩子站起来,是个哑巴,用手语比划着。
林晓翻译给大家听:
“我相信,当我无法说话时,
还有人愿意等我说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