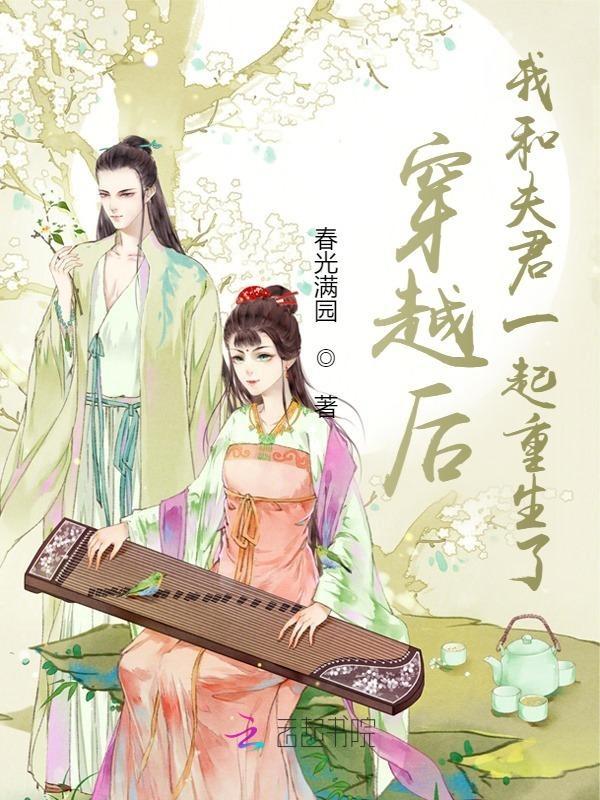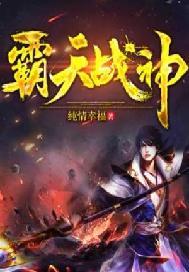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红楼之黛玉长嫂 > 186第 186 章(第1页)
186第 186 章(第1页)
正月十五,上元灯节。京城张灯结彩,火树银花不夜天。太液池畔搭起百丈灯廊,千盏琉璃灯映得湖面如星河倒悬。皇帝亲临观灯,命百官携眷同游,以示与民同乐。黛玉本欲推辞,周砚之却执她手道:“你已避世太久,今夜不妨随我走一遭人间烟火。”她终是点头应允。
入夜后,二人并肩缓行于灯市之中。百姓见之,纷纷驻足遥望,有人低语:“那便是林姑娘罢?听说她昨儿又参倒了一个户部郎中。”“可不是么,连宰相家的侄子都被她查了田契,抄了庄子。”“可敬可畏啊……”话音未落,忽有一童子提着一盏莲花灯跑过,口中哼唱着新编的俚曲:“明慧书院开东墙,女儿也能写奏章;不绣鸳鸯不拜堂,要替朝廷清库粮。”黛玉闻言微微一笑,俯身摸了摸孩子的头,取出一枚铜钱放入其灯篮。
行至一处灯谜摊前,周砚之驻足,指着一盏绘有山河图样的灯笼道:“这谜面写着‘天下为公’,打一官职名。”黛玉略一凝思,轻声道:“可是‘肃贪院主事’?”摊主拊掌大笑:“正是!姑娘好眼力!”周砚之侧目看她,眸中含笑:“你如今走到哪儿,都像是在审案子。”她亦笑:“若非心中常念此二字,怕是早被这满城灯火迷了方向。”
话音刚落,忽闻远处一阵骚动。只见数名锦衣卫押着一人穿街而来,那人披头散发,口中犹自高呼:“我无罪!我是被陷害的!林黛玉勾结僧人伪造账册,欲倾覆朝纲!”人群哗然四散,唯黛玉立定不动,目光冷峻。周砚之欲上前拦阻,却被她轻轻按住手臂。
“让他喊。”她说,“让天下人都听见。”
那人正是原湖广布政使赵文?,曾位列三品,掌一方民政赋税。《赋税实录》中首揭其家族虚报荒地、私征苛捐之事,牵连七州二十九县。前日已被革职下狱,今夜竟不知何故被押解过市。黛玉静静望着他扭曲的脸,忽而开口:“赵大人,你可知那十二万亩良田上,曾有多少农户因交不起租税而卖儿鬻女?你可记得有个叫阿禾的孩子,六岁便被卖去窑厂烧砖,活活累死在灶口边?他的母亲抱着尸骨跪了三日,无人问津。”
赵文?猛然转头,眼中凶光暴涨:“妖女!是你毁我功名,断我仕途!我一家三代忠良,岂容你凭一本野书便定罪?”
“野书?”黛玉从袖中取出一页泛黄纸片,展开于灯下,“这是你在万历三十七年亲笔所签的‘免税批文’,盖有湖广总督印信。可你隐瞒的是??那片田地根本不在荒册之内,而是强夺民产,转作私庄。十年来,你家每年暗收租米八万余石,折银近二十万两。这些钱,可有一文用于赈灾、修渠、助学?”
赵文?哑口无言,面色由红转白,继而瘫软在地。锦衣卫将其拖走时,他仍嘶吼不止,声如困兽。围观百姓沉默良久,终有人叹息:“原来清官难做,贪官更难防。”
归途中,风渐起,吹散了灯影重重。黛玉裹紧披风,低声道:“他们越是咆哮,越说明我们踩到了根子上。”周砚之颔首:“但也要小心反扑。今日之举,恐非寻常押解,倒像是有人故意安排,让你当众受辱。”她默然片刻,只说了一句:“只要真相还在纸上,羞辱便伤不到我。”
次日清晨,肃贪院议事厅内烛火未熄。慧空和尚盘坐案前,手中拂尘轻扫卷宗,神情肃穆。三位大臣已到齐,正争论是否应将涉案官员一律革职流放。黛玉端坐主位,声音清冷如霜:“律法自有尺度,不可因愤恨而滥罚,亦不可因情面而宽纵。凡查实贪污十万两以上、致民死伤者,斩;以下者,依数额论罪,追赃没产,子孙三代不得入仕。至于包庇徇私、篡改账册者,无论品级,一律削籍为民,永不录用。”
众人皆惊。一名老臣颤声道:“此令一出,恐牵连过广,动摇国本啊!”黛玉抬眸直视:“若国本建立在欺压百姓之上,那这国本本身便是毒瘤。与其苟延残喘,不如刮骨疗毒。”
正议间,张越急步而入,脸色铁青:“姑娘,江南来报??王夫人死了。”
厅内骤静。黛玉指尖微颤,却未动声色:“怎么死的?”
“据说是暴病身亡,棺木已封。可紫绡派去的人发现,她房中残留药渣含有‘断肠草’成分,且枕下藏有一封未寄出的信,提及‘事败露,恐遭灭口’。更蹊跷的是,办理丧事的嬷嬷昨夜也吊死在柴房,颈上绳索却是从背后勒紧的??分明是他杀。”
慧空低声诵佛:“因果循环,报应不爽。但她既死,线索恐断。”
黛玉缓缓起身,走到窗前。春寒料峭,檐下冰凌滴水成珠。她望着那一串串坠落的水滴,忽然道:“不会断。只要还有人在寻找真相,就没有真正的终结。”她转身下令:“即刻调集江南十三府近五年刑案卷宗,重点核查所有‘暴毙’‘自尽’之人,尤其是曾与贾府、王府有关联者。另,命密探潜入那处庄园,掘地三尺,也要找出她生前最后接触过的人。”
三日后,消息传来:庄园地窖中挖出一口铁箱,内有数十份契约文书,记载着当年贾府如何通过高利贷逼死平民、强占田产;更有几封密信,显示王夫人曾多次贿赂巡抚衙门,掩盖其弟挪用军饷之事。最令人震惊的是一本日记残页,上面写着:“宝玉痴傻非天生,乃服药所致。彼时林氏孤女难控,唯有使其未婚夫心智受损,方可保我儿嫡位安稳。”
黛玉读至此处,手中茶盏落地碎裂。紫绡扑通跪下,泣不成声:“姑娘……对不起,我早该告诉您……姐姐紫鹃临死前,曾偷偷托人送来半块玉佩,说是宝玉被人下了慢性毒药,每日饮的参汤里掺了‘迷心散’……可我当时年幼,不懂其中深意,等到明白时,姐姐已经……”
黛玉扶起她,双目赤红,却异常冷静:“不是你的错。是我们都被蒙在鼓里太久。”她提笔疾书,一道奏疏直呈御前,请求彻查贾府旧案,并召还当年被贬谪的几位清廉官员作证。皇帝览疏良久,朱笔批下八个大字:“沉冤必雪,奸佞必诛。”
二月初八,春雷始鸣。朝廷正式下诏,重审贾府旧案。昔日依附王府、参与构陷的官吏十余人下狱,贾政虽未直接涉案,但因知情不报、纵容家人作恶,被削去爵位,贬为庶民。宝玉则由太医会诊,确认确因长期服用药物导致神志不清,经停药调理,已有苏醒迹象。
消息传至贾母耳中,老人当场昏厥,醒来后喃喃道:“我对不起黛玉……我对不起她娘……”临终前唯一遗愿,是请黛玉入府一见。黛玉去了。她站在垂暮老人床前,听她断续诉说当年如何被王夫人蒙蔽,如何眼睁睁看着贾敏嫁入林家后遭排挤孤立,最终郁郁而终。“我本想护你周全……可我太懦弱……”贾母握住她的手,泪流满面。
黛玉轻轻替她掖好被角,低声道:“老太太,我不怪您。在这世上,最难的从来不是作恶,而是坚持善良。您能醒悟,已是不易。”
贾母含泪而逝。黛玉为其守灵一夜,焚香三炷,诵《心经》一遍。翌日,她将贾府祖产中属于林家陪嫁的部分尽数退还给地方官府,用于修建义学与医馆。她在文书末尾写道:“恩怨已了,往事如烟。唯愿此后,再无门户之争,再无妇孺受欺。”
三月中旬,明慧书院正式开课。首批招收孤贫女子一百二十人,年龄自八岁至二十不等。黛玉亲任山长,每周授课两日,讲授律法基础与民生实务。第一堂课上,她站在讲台前,面对一双双渴求的眼睛,缓缓说道:“你们之中,或许有人曾被人说‘女子识字无用’,或许有人因贫穷被迫辍学、早嫁、劳作至死。但今天,我要告诉你们??知识不属于任何性别,它属于每一个不甘命运摆布的灵魂。”
台下寂静无声,唯有泪水滑落的声音。一个十岁的小女孩举起手,怯生生地问:“先生,我们真的能当官吗?”黛玉走下台阶,蹲在她面前,认真回答:“不仅能当,而且必须当。因为这个世界缺的不是男人,而是公正。而公正,需要无数双眼睛去看,无数双手去撑。”
课后,周砚之在校门外等她。春风拂面,柳絮纷飞。他递上一杯热茶,笑道:“你今日说话的样子,像极了当年在朔州城头训兵时的我。”她抿嘴一笑:“那你是不是觉得,我也该披甲执剑了?”他摇头:“你早已披甲,那是信念;你早已执剑,那是笔墨。”
四月初五,清明雨上。黛玉率肃贪院诸人赴郊外祭扫十七义民之墓。沿途百姓自发设香案祭拜,孩童献花,老者焚纸。她立于碑前,宣读最新政令:全国各县设立“民告官”信箱,凡百姓举报贪腐,无论真假,三日内必有回音;属实者重奖,诬告者依法惩处,但不得株连家属。同时宣布,三年内完成全国土地清丈,推行“均田减赋”新政,使耕者有其田,贫者有所依。
当晚归府,她伏案整理各地奏报,直至更深。忽觉肩头一暖,回头见周砚之为她披上外袍,手中端着一碗姜汤。“喝点暖暖身子。”他说,“你可知今日书院里的学生给你起了个称呼?”她挑眉:“什么?”“她们叫你‘林先生’。”
她怔住,眼眶忽热。良久,才轻声说:“父亲若听到,定会很高兴。”
五月初十,夏初炎炎。盐行会运行半年,成效显著。国库增收之余,民间盐价稳定,百姓不再因缺盐而患病。皇帝特赐黛玉黄金百两、绸缎千匹,以示嘉奖。她尽数转赠明慧书院,用于扩建校舍。与此同时,惠妃在狱中绝食七日,终不肯招供幕后同党。审讯官回报:“她只说,‘成王败寇,何必多言’。”
黛玉亲自前往天牢探视。惠妃蓬头垢面,瘦骨嶙峋,见她进来,冷笑不已:“你赢了。如今万人敬仰,风光无限。可你有没有想过,你所做的一切,不过是换了一批人掌权?十年后,照样会有新的贪官,新的冤魂。”
黛玉静静坐下,取出一幅地图铺于桌上:“你看,这是全国三十四州盐行会分布图。每一处红点,代表一个由百姓推选的监督委员。他们有权查阅账目、质询官员、提出罢免。这不是权力更替,而是制度重生。你所谓的‘循环’,正在被打破。”
惠妃盯着地图,眼神渐变,终是闭目长叹:“罢了……我输了。但我告诉你一句话??权力之下,没有纯粹的善。你今日以为自己为民请命,将来也会被别人视为挡路的石碑。”
“那又如何?”黛玉起身,“只要我还站着,这块碑就不会倒。”
出狱后,她写下《监察条例》七章二十八条,呈请皇帝钦定为永久律法。其中规定:凡肃贪院官员任期不得超过三年,期满轮换;所有调查过程必须公开摘要,接受士绅评议;严禁以政治斗争之名行报复之实。她在附注中写道:“正义若失去约束,便会变成另一种暴政。”
六月初六,芒种时节。明慧书院首届学生举行结业考。三十名优等生将被派往偏远州县,担任助理账房或基层巡检。临行前,黛玉为她们每人赠书一本《贞观政要》,并在扉页题字:“持正守心,不负苍生。”
那一夜,她梦见父亲站在江南庭院中,手持一本书,微笑道:“玉儿,你做得很好。”醒来时,窗外晨光初露,鸟鸣清脆。她提笔写下一封家书,寄往苏州祖坟:“父亲,女儿未辱家风。山河清明之路漫长,但我始终在路上。”
周砚之走进书房,见她伏案而眠,便轻轻取过披风为她盖上。他凝视着她憔悴却坚定的侧脸,心中默念:这一生,我愿做你跋涉千山时脚下的路,抵御风雪时头顶的天。
钟楼再度响起晨钟,悠远绵长,仿佛回应着除夕那夜的誓言。长安城渐渐苏醒,新的一天开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