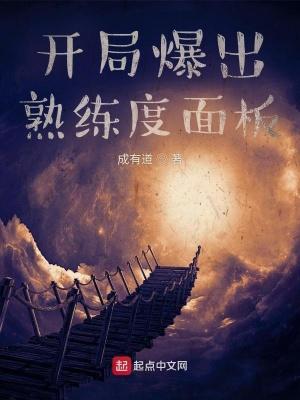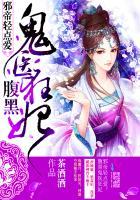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金殿销香 > 293罗织(第1页)
293罗织(第1页)
春深似海,慈光寺的杏花开了又谢,落英铺满石阶。照雪每日清晨扫去花瓣,不令其腐于尘泥。她素手执帚,袈裟拂地,眉目间依旧如雪峰静立,可眼底已无当年孤绝之色。十年光阴,足以让一座荒寺化作道场,也足以让一段血仇化为慈悲。
那一夜楚恒沂驾崩后,五位公主各自归位:阿箬主掌太医院,编纂《千金续方》,专录民间验方;明心入翰林修史局,主持修订《大楚律疏》,更将佛门因果与律法条文相融,创“心证”之说??凡重案必察被告心迹,不得滥施酷刑;婉柔升任尚书左仆射,为开国以来首位女宰相,朝中称“女相公”;昭蘅则奉旨巡抚西北七州,督建水利、安抚羌戎,百姓呼为“玉关娘子”;唯有照雪,始终居于慈光寺,诵经行医,不涉权柄。
然而,风平浪静之下,暗流未息。
某日黄昏,一名衣衫褴褛的老妇被抬进慈光寺山门,高烧不退,唇舌生疮,脉象浮数如沸。照雪亲自施针用药,三日后方醒。老妇睁眼第一句便是:“菩萨……我不是来求医的,我是来还债的。”
她自称姓陈,原是冷宫旧役,二十年前那场大火当晚,她正在廊下值夜。她说自己亲眼看见陆九德提灯而来,身后跟着两名黑衣人,抬着一只铁箱。箱中并非账册,而是几包火油与硫磺。他们将油洒在帷帐角落,又在门窗缝隙塞入浸药棉絮,最后点燃引信离去。而所谓“失火”的嫔妃,实则是被灌下迷药后拖入火场,伪装成逃窜不及的模样。
“我本想告发,可第二天就被人调离冷宫,发配去守皇陵。”老妇颤声道,“后来听说,凡是那夜当值却活下来的宫人,不是暴毙,就是疯癫……我装傻三十年,今日才敢开口。”
照雪听罢,久久不语。她取出那只绣鞋内衬的残片,与老妇所言一一对照,竟分毫不差。更令人惊心的是,老妇还提到一个名字??黄门监副使周怀安,当时负责记录各宫灯火出入,曾私下记下陆九德那晚进出冷宫的时间,并藏于家中梁上。
“他儿子如今在刑部做书吏。”老妇低语,“若要查证,或可从他入手。”
照雪当即修书一封,命弟子连夜送往京城。次日清晨,阿箬便带着两名太医赶到慈光寺,面色凝重。
“姐姐,”她握住照雪的手,“昨夜刑部接到匿名投书,正是周怀安之子所献??他父亲留下的日记原件,详细记载了宁安如何通过陆九德操控内廷事务,甚至包括……张慧妃中毒一事。”
“什么?”照雪指尖微颤。
阿箬点头:“原来当年张慧妃并非单纯难产而亡,而是被人在安胎药中掺入微量鹤顶红,日积月累,损及心脉。真正开方的太医早已被灭口,替换成了宁安的人。而那位太医的女儿,现就在义塾教书,名叫沈清漪。”
照雪闭目良久,终轻叹一声:“原来我们以为终结的往事,只是掀开了第一章。”
此事迅速惊动朝堂。婉柔立即下令重启“昭雪司”特别议程,召集三法司会审。明心亲自主持笔录整理,逐条核对史料档案。三个月内,翻查旧档三千余卷,传唤幸存宫人四十七名,最终拼凑出一幅骇人图景:
宁安并非孤身作乱,而是一个庞大阴谋网络的核心。她利用先帝晚年多疑之心,勾结内侍、收买御医、操纵选秀,逐步清除异己。冷宫大火只是冰山一角,十年间至少有十二起“意外死亡”实为谋杀,受害者皆与张慧妃亲近,或知晓其真实死因。
最令人痛心者,竟是当年替张慧妃接生的稳婆李嬷嬷。她在临终前写下血书,藏于佛龛夹层,却被宁安亲信搜出焚毁。其孙女侥幸逃脱,流落江南,靠刺绣为生,直至近年才得知祖母冤情,冒死上书。
婉柔读完供词,泪落如雨。她在政事堂当众宣布:“此非merely追究旧案,而是向天下昭示??谎言筑起的荣耀,终将崩塌;而沉默堆积的罪恶,必须清算。”
于是,一道诏令颁行全国:凡参与宁安阴谋者,无论生死,一律追贬削籍;其子孙三代禁仕;涉案官员墓碑除名,祠堂拆毁。同时,设立“贞悯祠”,供奉所有蒙冤宫人牌位,每年清明由皇室亲祭。
百姓闻之,无不称快。街头巷尾流传新童谣:“金殿销香烟袅袅,冤魂今日得归家。莫道宫深无天日,五明照夜破云霞。”
可风波并未止歇。
就在“贞悯祠”落成当日,一名年轻女子跪于祠前,手持半块龙纹玉佩,自称是李嬷嬷的孙女沈氏,请求面见陛下??但她要见的,不是已逝的楚恒沂,而是当今太子楚砚。
原来,自楚砚现身认祖归宗后,因其聪慧果决,深得仁宗喜爱,早立为储君。如今已年满二十,监国理政,颇有乃祖之风。他听闻此事,当即亲赴祠堂,扶起女子。
“你说你是沈清漪?”他问。
女子含泪点头:“先祖李氏,为张慧妃接生时目睹真相,遭宁安构陷,全家流放岭南。途中冻饿交加,仅我母一人幸存,嫁与当地郎中,生下于我。我自幼习医,考入义塾,后入太医院为婢,不敢言出身,唯恐牵连他人。”
楚砚沉吟片刻,忽然问道:“你可知……为何宁安非要置张慧妃于死地?”
沈清漪摇头。
楚砚缓缓从袖中取出一封信,泛黄纸页上字迹娟秀,却是女子笔迹:“这是我母亲柳疏影临终前所写。她说,张慧妃怀胎十月时,曾请一位西域游方僧人观相。那人断言:‘此子若生,必承天命,改写国运。’宁安得知后,惧怕真龙降世动摇她的布局,遂下毒手。”
众人皆惊。
阿箬失声:“所以……父皇的早逝,并非偶然?”
楚砚点头:“母亲说,宁安原本计划在张慧妃生产当夜动手,但因阵雨延误,只得改为慢性毒杀。而真正的致命一击,是在婴儿出生后第三日,借‘洗三’之礼,在水中加入蚀骨散,意图让新生儿七日内悄然夭折。幸而李嬷嬷察觉水色异常,偷偷换盆,又谎称孩子体弱需避风,将其藏入暖阁七日,才保住性命。”
“那孩子……是谁?”昭蘅急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