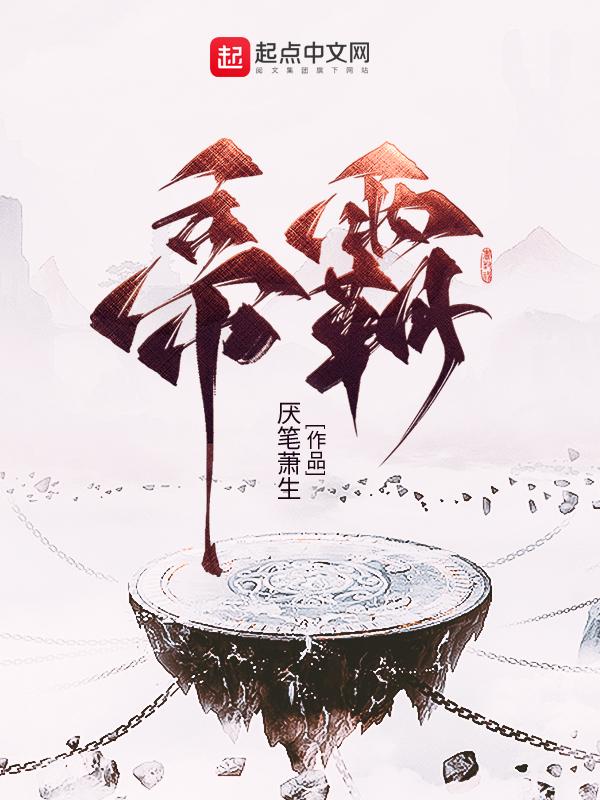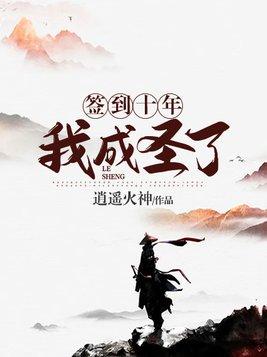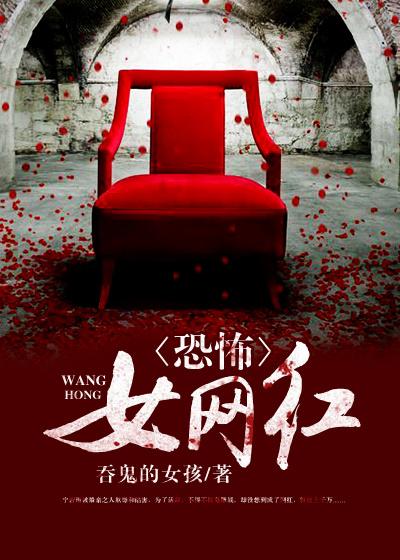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步步高升:从省考状元到权力巅峰 > 第541章 要讲个师出有名(第1页)
第541章 要讲个师出有名(第1页)
“保哥,派出所将人已经发出来了。受伤的几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。政府没有忽悠我们。”
“知道了!”
董天保微微颔首。
政府的应对措施让董天保颇为意外。
他原本以为今天这个事情会愈演愈烈,一发不可收拾。
没想到,政府表现得十分宽容。
坐在董天保对面的是一个女记者,她豁然起身,皱眉道,“董老板,今天这个事情,我们无法按照原来的计划出稿了。你们县政府部门面对危机公关表现得很成熟。如果我们按照原来的稿件写的话,编。。。。。。
唐烨的改革之风吹遍了全国科技系统,但正如他所料,这场深层次的变革也触动了不少既得利益者的神经。尤其是《科研成果分类评价办法》实施后,一些长期依赖论文数量、项目经费规模获取职称晋升与资源分配的科研单位开始出现反弹。
最先跳出来反对的是中科院下属某研究所的一位资深院士??陈启明。他在一次学术论坛上公开批评:“这种分类评价看似公平,实则削弱了基础研究的权威性,让真正沉下心来做学问的人反而吃亏。”
这番言论迅速在网络上发酵,支持者认为“学术本就该以国际影响力和论文质量说话”,而反对者则指出“过去几十年中国科研之所以能追赶世界水平,靠的就是高强度、高密度的产出”。
面对舆论压力,林婉清第一时间向唐烨汇报情况,并建议召开专家座谈会进行政策解释与沟通。唐烨却摇了摇头:“我们不能总是被动回应,而是要主动出击。”
于是,在一次国务院主持的科技创新座谈会上,唐烨当着数十位顶尖科学家、高校校长与企业代表的面,亲自阐述了这项改革的初衷与目标。
“过去我们强调‘多出成果、快出成果’,这是特定历史阶段的需要。”他语气沉稳,“但现在,我们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,不能再用粗放式的方式去衡量科研的价值。”
他顿了顿,目光扫过全场:“基础研究固然重要,但它不是唯一的赛道。应用型研究解决实际问题,技术转化推动产业升级,这些同样是国家所需、人民所盼。”
会场上一片沉默。片刻后,一位年近七旬的老教授缓缓开口:“唐部长说得没错。我做了一辈子理论物理研究,但我也不得不承认,这些年我们的许多论文只是在实验室里打转,真正落地的太少。”
这位老教授的话仿佛打开了一扇窗,几位来自企业的代表纷纷发言,讲述他们在技术研发过程中遇到的瓶颈,以及与高校合作时的种种障碍。
“很多时候,不是我们不愿意转化,而是科研评价体系不允许。”一家新能源企业的总工程师感慨道,“教授们更愿意发SCI文章,而不是跟我们一起去车间解决问题。”
唐烨听后微微一笑:“所以,我们必须改变这套游戏规则。”
座谈会结束后,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刊发评论员文章《科研评价改革势在必行》,文中明确指出:“科技强国不只是论文大国,更是创新强国、产业强国。”
与此同时,科技部联合教育部启动“科研成果转化激励计划”,设立专项基金,鼓励高校、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,并对成功实现技术转化的团队给予额外奖励。
这一系列举措再次引发学界震动。不少青年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方向,部分原本专注于发论文的团队也开始尝试与企业对接。
然而,就在改革稳步推进之际,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悄然逼近。
某日清晨,唐烨刚走进办公室,林婉清便急匆匆地送来一份紧急报告:某国家级半导体材料研发项目的核心数据疑似泄露,涉及多个关键技术参数,极有可能已被境外势力获取。
“目前尚未确认是人为泄密还是网络攻击。”林婉清神色凝重,“但初步调查显示,该项目组一名年轻研究员近期频繁出入国外使馆区域,行为异常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