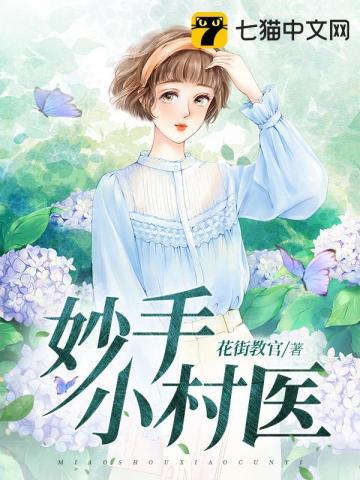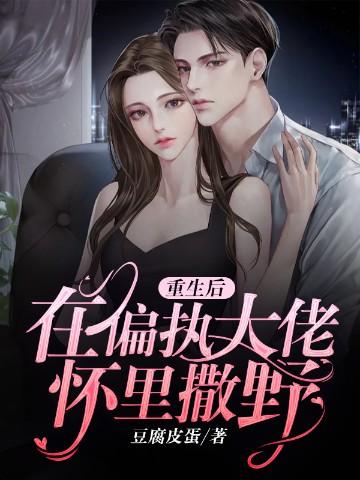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刚想艺考你说我跑了半辈子龙套? > 第475章 这个角色陈瑾是演爽了(第2页)
第475章 这个角色陈瑾是演爽了(第2页)
>而一声准时响起的公交报站,竟成了某个灵魂活下去的理由。
>
>我们总在寻找伟大的定义。
>可或许,伟大就是:
>明知无人注视,仍把一件事做到极致;
>明知世界冷漠,仍愿为陌生人留一盏灯。
>
>这本书里的每一个人,都没有改变历史。
>但他们让每一天的历史,得以平稳前行。
>他们不是时代的主角,却是支撑时代不塌陷的脊梁。
>
>所以,请允许我用最朴素的语言致敬:
>谢谢你们,在我看不见的地方,活成了光。
写完最后一个字,已是凌晨三点。他将稿件发给主编,转身走向阳台。远处,第一缕晨光正刺破云层,洒在城市的屋檐之上。
几天后,新一期拍摄计划启动。目标是一位名叫沈秀兰的殡仪馆遗容修复师。五十岁,从业二十八年,经她hands整理过的逝者超过四千人。网上关于她的信息极少,唯一一条采访视频也只有三十秒:“我只是想让他们走得体面一点。”
林默提前一周预约,终于获准进入工作区旁观一次修复过程。
那天下午,天气阴沉。太平间外走廊寂静无声,只有消毒水气味弥漫在空气中。沈秀兰身穿浅灰色制服,戴着口罩,眼神平静如水。躺在操作台上的是一位因车祸离世的年轻人,面部受损严重。
她轻轻擦拭每一寸皮肤,剪去凌乱的头发,用特制蜡填补创口,再一点点描画眉毛与唇色。整个过程持续近三个小时,她几乎没有停顿,动作精准得像在完成一件艺术品。
“家属说,他生前最爱笑。”她一边调色一边轻声说,“所以我要让他看起来像是刚做完美梦醒来。”
林默站在玻璃窗外,透过单向镜注视这一切。他的喉咙发紧,几乎无法呼吸。这不是死亡的终点,而是一场庄严的告别仪式,由一位平凡女人默默主持。
结束后,他在休息室见到沈秀兰。她脱下口罩,脸上刻着岁月的痕迹,眼角却带着温柔笑意。
“怕吗?”她问他。
“怕。”林默诚实回答,“但我更敬佩您。”
“其实我也怕。”她说,“第一次接手婴儿遗体时,我哭了三天。可后来我想通了??如果我们都不敢面对死亡,活着的人该怎么办?”
她翻开一本相册,里面全是修复前后对比照。每一张背面都写着一句话:“请记住他她曾如何爱这个世界。”
“你知道吗?”她合上相册,“很多人觉得我的工作晦气。可我觉得,我是最后一道门的守护者。亲人最后一眼看到的面孔是我给的,这份责任,比任何荣耀都重。”
林默回去后整夜未眠。他翻出所有素材,重新剪辑了一支短片,命名为《最后一面》。没有背景音乐,只有她低柔的声音贯穿始终:
>“我会为你梳头,因为你妈妈说你从小就不爱扎辫子;
>我会擦掉血迹,因为你的孩子还不懂什么叫意外;
>我会闭上你的眼睛,是因为我知道,你也想安心睡去。”
视频上线当天,评论区涌入无数留言:
>“我爸走的时候,是沈老师做的修复。她说‘他很安详’,我妈抱着她哭了好久。”
>
>“我在医院实习,看完这个决定转临终关怀科。原来温柔也可以是一种职业。”
>
>“我报名了志愿者培训,想学基础遗容护理。虽然不敢保证能做好,但我想试试。”
林默看着这些文字,忽然接到一个陌生来电。号码归属地是云南山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