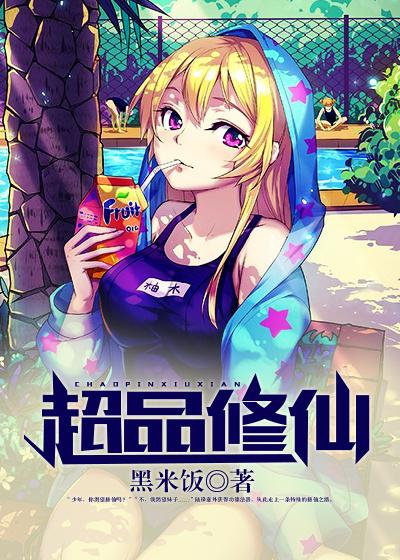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我真没想下围棋啊! > 第四百八十七章 现在我要继续走下去(第1页)
第四百八十七章 现在我要继续走下去(第1页)
而在荒木野与安弘石这盘棋结束的同时,不远处人群,也突然响起一阵骚动。
俞邵扭头望去,只见苏以明缓缓站起身来,也向俞邵投来视线,眼神中带着一丝坚决的斗志。
虽然没看那盘棋,但当看到苏以明的眼。。。
夜色像墨汁滴入清水,缓缓漫过城市天际。我坐在书桌前,手指悬在键盘上,迟迟没有敲下第一个字。《该我了》这三个字在我脑海里盘旋已久,却始终不敢落笔??仿佛一旦写下,就等于正式向过去告别,也等于承认,这一路走来的所有沉默、泪水与微光,终将凝固成纸上的句点。
窗外风起,吹动那瓶沙漠沙轻轻晃荡,细小的颗粒在斜阳余晖中闪烁,宛如星屑浮动。我想起沈砚之说的那句话:“最渺小的存在,也可能承载过宇宙的重量。”此刻,这粒粒黄沙,那枚压在小男孩留言上的白子,还有阿?用火塘灰画出的棋格,都成了某种不可言说的证物,证明着那些未曾被听见的声音,确确实实存在过。
手机震动起来,是李小川妈妈发来的语音消息。她声音有些哽咽:“沈老师昨天去了学校……没说什么,就坐在教室后面听了一节课。课间他把我儿子叫出去,在操场上摆了个简易棋盘,教他‘双打吃’。临走时留下一本旧棋谱,扉页写着‘不怕输的人,才配赢’。”
我的心猛地一颤。
沈砚之从来不说重话,可他的行动总是比言语更沉。他不是去鼓励一个孩子,他是以一种近乎仪式的方式,把“弈心”悄悄种进泥土里,等着它自己破土而出。
我打开录音笔,翻出去年冬天在云南山村录的一段音频。那是除夕夜,火塘边,一位失明老人正和孙子对弈。没有棋盘,也没有棋子,他们用手势比划,用口述推进??
“爷爷,我跳尖守角了。”
“嗯,好。那我飞挂右上。”
“哎呀!你挖断我啦!”
“哈哈,这叫‘老树盘根’,三十年前我在县文化馆赢冠军就靠这一手。”
祖孙俩笑作一团,火苗噼啪作响。那一刻,胜负早已无关紧要,重要的是,有人愿意陪你虚构一场真实的对局,哪怕只是用声音搭建起一座虚幻的棋城。
我把这段录音放进策划案附件,又调出一张照片:青海湖畔渔村的地图,上面标着几个红点,其中一个写着“达日玛老人??鱼骨棋传人”。据说他年轻时曾随父亲驾船捕鱼,一次风暴后船只倾覆,唯有他抱着一块浮木活了下来。此后每年清明,他都会用捡来的鱼骨打磨成黑白棋子,摆于湖岸石台上,说是“给亡魂陪一局”。
我不知道这样的故事还能不能打动今天的读者。这个时代太吵了,人们习惯快节奏、强冲突、戏剧性反转。而我所记录的,不过是一个老人对着空椅说“轮到你了”,或是一个环卫工阿姨午休时蹲在台阶上,拿粉笔在地上画个九路棋盘,和陌生人下完一局再默默擦掉。
可正是这些轻如尘埃的瞬间,让我一次次停下脚步。
第二天清晨,我背上相机和笔记本,独自重返H口。棋桌已被重新漆过,边缘刻着一行小字:“愿落子有声,声声入心。”一群小学生围着桌子叽叽喳喳地争论定式,有个小女孩举着手里的塑料棋子问同伴:“你说,如果黑棋不想赢呢?”
我驻足聆听。
她说:“有时候我觉得,下棋不是为了打败谁,而是想告诉对面那个人??你看,我还在这儿。”
这句话像一把钥匙,猝然打开了我心里最后一道门。
我坐在长椅上,掏出本子开始写:
>**《该我了》**
>那天展览结束后的雨停了,我们收起棋具,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。我以为旅程就此落幕,直到那个撑红伞的小男孩写下那句话:
>“我想和爸爸下一盘棋,但他总说忙。”
>我突然明白,所谓“民间棋心”,从不在于技艺高低,而在于那一声微弱却执拗的呼唤??
>“你能听见我吗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