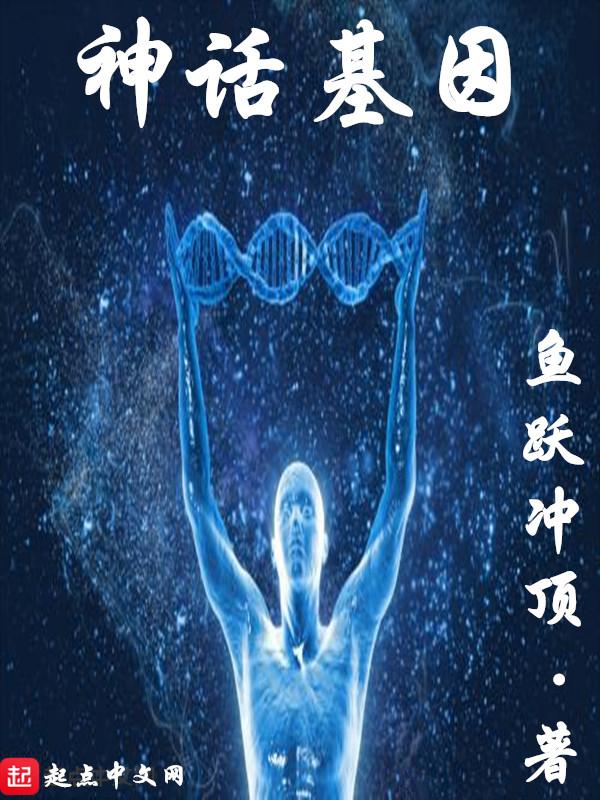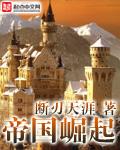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剑走偏锋的大明 > 第九百六十章 我也要学(第1页)
第九百六十章 我也要学(第1页)
太热闹了,国子监东侧门也站满了人,都在排队进去,旁边还有好多衣衫普通的老百姓,一双眼睛虚虚的左看右看,看到潘岳身上的国子监服,就迅速移开眼睛,也不搭理被潘岳抓着手的潘筠,而是紧紧盯着跟在他们身后的妙真。。。
暴雨在午夜倾泻而下,如天河倒悬,砸在孤岛茅屋的瓦片上,发出沉闷而连绵的声响。沈兰舟未眠,独坐灯下,手中握着一支细炭笔,在《民权初论》的末页写下最后一段批注:“火种既播,风自不息;人可隐,道不可灭。”她搁笔良久,望着窗外电光撕裂天幕,仿佛看见十年前雪峰之巅那场大火??黑衣娘率影卫断后,烈焰吞没山道,只为让三百流民逃出生天。
那一夜,她焚去玉蝉,也焚尽了以血还血的旧誓。从此不再藏身暗处,却也未曾现身明堂。她只是将思想化作文字,把制度铸为阶梯,一步步推着这腐朽江山向微光前行。
翌日雨歇,海面浮起薄雾,如同思绪缭绕不散。新来的渔家孩童照例聚集书屋前,踩着湿漉漉的石板蹦跳嬉闹。那个曾问“什么是公平”的小女孩捧着一本用粗麻纸装订的小册子跑进来,满脸兴奋:“先生!我们自己写了‘村规’!”
沈兰舟接过一看,竟是孩子们模仿《议事会章程》所拟的一份“学堂公约”:每日轮流扫地、借书需登记、吵架要当众讲理、大孩子不得欺负小孩子……字迹歪斜,却一笔一划极为认真。她轻轻抚过纸页,眼中泛起温润光泽。
“你们知道吗?”她缓缓开口,“当年我姐姐教我的第一件事,就是写一张契约??两个孩子约定交换竹蜻蜓,白纸黑字,按手印为证。她说,哪怕最微小的承诺,一旦写下,就有了重量。”
孩子们安静下来,屏息听着。
“所以,你们写的不是游戏,是规则的种子。它今天管一间学堂,明天或许就能管一个村子、一座城。只要人们相信‘说好了就得算数’,公义就不会消失。”
正说着,远处传来脚步声。一名面色黝黑的青年男子踏着晨露而来,肩披蓑衣,怀里紧抱一只防水油布包。他是福建分院派来的联络员,名叫陈砚,原是泉州港的抄账小吏,因揭露税监虚报船税被革职追捕,后得赤莲弟子相救,自此投身“组织之法”的传播。
他进屋便跪地行礼,声音颤抖:“先生……吕宋出事了。”
沈兰舟神色不动,只轻声道:“坐下说。”
陈砚喘息片刻,打开油布包,取出三封信笺与一幅染血的地图。他语速急促:“海莲塾昨年已扩至五处,女学生们不仅识字算账,还帮华侨商户立合同、调纠纷。上月更牵头成立‘商妇会’,集资购船运货,绕开关卡盘剥。此举触怒当地西班牙总督府,以‘聚众谋逆’为由查封学堂,拘禁七名教师,其中两人……被打死在狱中。”
屋内骤然寂静。窗外海浪拍岸,一声声如心跳。
“他们烧了我们的书,”陈砚咬牙切齿,“但烧不掉人心。昨晚有三百华侨围堵衙门,举着《民权初论》残页高呼‘我们要说话的权利’!西人出动火枪队镇压,死伤数十,可仍有人趁夜潜入监狱,救出四人。这是幸存者口述的全过程。”
沈兰舟接过地图,上面标注了海莲塾位置、巡逻路线与牢狱结构,边缘密密麻麻写满笔记,字迹竟是沈兰漪的手笔风格。她心头一震。
“这字……是你姐留下的?”陈砚低声道,“她在吕宋待过三个月,临走前亲手交给一位老渔民保管。她说,若有一天赤莲之火传到南洋,就请代为转交。”
沈兰舟指尖微颤,久久凝视那熟悉的笔锋。十年前乌镇桥头一别,沈兰漪远走海外,音讯全无。世人皆以为她投海自尽,唯有朱莲曾悄悄告诉她:“你姐活着,在看不见的地方,做着和你一样的事。”
原来如此。
她闭目深吸一口气,再睁眼时已清明如镜。“告诉吕宋的姐妹们,不必复仇,但也不能退缩。我要她们立刻组建‘国际申诉团’,收集暴行证据,翻译成西班牙文、拉丁文,送往马尼拉教会、葡萄牙商馆、甚至罗马教廷。同时联络日本、暹罗的华侨商会,发起联合抵制西班牙货物运动。”
陈砚愕然:“可他们听不懂我们的道理啊!”
“那就让他们听得懂利益。”沈兰舟站起身,走到墙边悬挂的世界海图前,指尖划过航线,“贸易依赖港口秩序,若西人残暴致商路中断,吃亏的是他们自己。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,压迫女子、焚毁学堂的行为,会让每一艘驶向吕宋的商船减少三成利润。资本比刀剑更怕损失。”
她转身盯着陈砚:“另外,选三位能言善辩的女学生,训练她们撰写公开信、绘制图表、展示伤亡名单。半年之内,我要这事件震动里斯本与马德里。”
陈砚震撼不已,重重点头:“属下即刻动身。”
待其离去,沈兰舟独自伫立良久,终提笔修书两封。一封寄往扬州,嘱朱莲设法通过耶稣会士渠道将材料递至欧洲;另一封则发往辽东,提醒周承恩防范敌军借外患之机煽动边民叛乱??她早已察觉,朝廷虽采《边策十二要》,但地方官仍多敷衍塞责,乡勇缺饷少械,隐患未除。
写罢,她推开木窗,见朝阳正破云而出,金光洒满海面。一群海鸟掠过礁石,飞向远方。她忽然想起万历十四年秋,张居正推行“一条鞭法”遇阻,六部官员联名弹劾其“变乱祖制”。彼时京城谣言四起,称首辅欲废科举、撤宗庙。危急之际,全国各地竟有百余所书院联名上书,引用《民权初论》中“税归总额、役随田定”之论,力挺新政,并附万民联署血印。
那一波浪潮,正是从这座孤岛出发。
如今,风已越重洋。
数月后,消息陆续传来:吕宋事件经欧洲传教士披露,引发荷兰、英国商人对西班牙垄断政策的不满,多国议会就此展开辩论;而福建沿海民间自发组织“护学船队”,每艘商船出航必载几名女塾生同行,形成流动学堂,官府不敢再轻易查扣。
与此同时,辽东果然爆发危机。鞑靼一部伪装成商队混入长城关口,意图里应外合夺取宁远。幸赖当地依《边策》建立的“烽哨网”,一名放羊少年发现异常踪迹,连夜点燃三堆狼烟,驻军及时布防,全歼敌探。战后,万历帝特赐少年“义民”称号,赏银百两。少年却将银钱捐出,请求在当地建一所“边童书屋”。
沈兰舟得知,只淡淡一笑:“民心可用,则万里边疆皆为铜墙。”
这一年冬,海上忽现异象。一艘来历不明的西洋帆船漂流至岛岸,船体破损,桅杆断裂,舱中仅存一名奄奄一息的老者。救回后才发现,竟是多年失踪的徐光启之师??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助手汤若望。他怀中紧抱一只铁盒,内藏一份手稿与一幅精密星图。
经半月调养,汤若望建恢复神智。他用半生不熟的汉语断续讲述:原来他奉罗马教廷之命东来,欲考察东方“异端思潮”,途中听闻赤莲书院事迹,特意绕道寻访,却遭葡萄牙舰队拦截,斥其“勾结叛党”,船只被毁,同伴尽殁。
“你们……不是暴徒。”他在病榻上喃喃,“你们教女人读书,教穷人写状,教士兵守土而不杀人……这不是造反,这是……新世界。”
沈兰舟亲自为其译述《民权初论》节本。汤若望听罢泪下:“我在欧洲见过启蒙之火,却被国王扑灭。而你们,在帝国边缘,默默点燃了它。”
临别时,他郑重递交那份手稿:“这是我二十年观测东方天文、地理、政情所记,名为《寰宇理志》。其中详述地球圆说、历法修正、机械原理。我知道你们不用这些来争权夺利,但可用它们打破愚昧。”
沈兰舟收下,回赠《新罪录》最终版复印件:“你也带一本回去。让西方知道,中国人不仅会忍耐,也会觉醒。”
汤若望归途病逝于澳门,但他留下的手稿十年后辗转流入江南匠人之手,催生出第一批改良火器与航海仪器,更间接促成“格物学会”兴起,主张“以实证求真知,以科技强国民”。
而孤岛上,沈兰舟并未停下脚步。她召集所有留守弟子,宣布启动“百年计划”:
一、编写《基础公民手册》,涵盖读写、算术、法律常识、公共卫生,作为各地学堂通用教材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