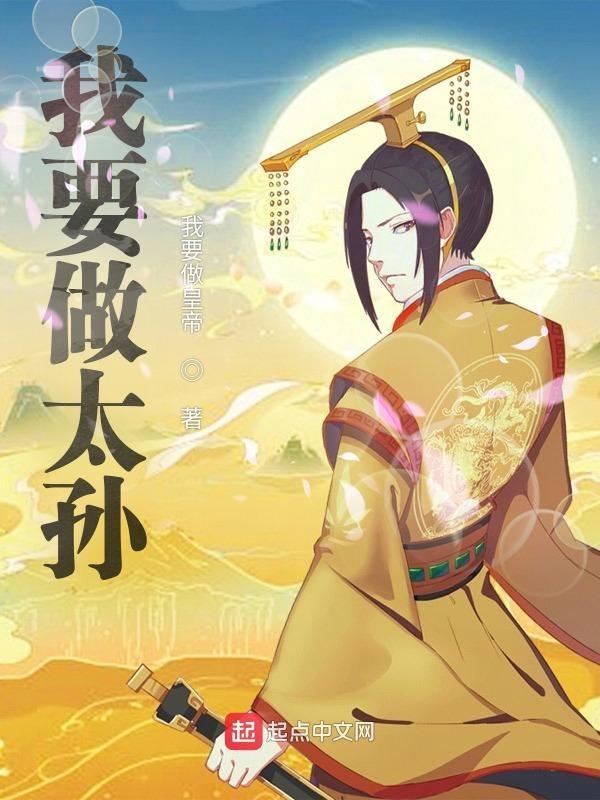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浪儿翻 > 5060(第18页)
5060(第18页)
最终为她战死沙场。
当他倒在雪地里的时候,腕间还绕着她的发绳。
他什么都不知道,他来这世上,仿佛只是为了把龙霈从沟渠里拉出来,带她看看月亮。在他眼里,龙霈不是北境王妃,不是谁的将领,也不是谁的母亲,她就是龙霈而已。
他珍爱的,如珠如宝的龙霈。
风卷起帘脚,晃出道黄色裙摆,阿勒把眼一瞥:“出来,学会听墙角了你,听得懂吗。”
龙可羡慢慢吞吞地挪步,手脚并用地爬上榻,然后乖乖地坐着听老仆讲故事,她方才总听到个龙字,总觉得与她有关系。
阿勒把她耳朵一捂,说:“怪不得,这小东西随她爹了。”
“您自个儿也小。”老仆念一句,不再说了,即便龙可羡听不明白,但对上那么双干净无辜的眼睛,他怕漏出些许情绪,再戳到了小姑娘的心。
龙可羡被捂住耳朵,哪哪都不舒坦,便挣扎起来,在阿勒跟前扭得厉害,阿勒反手往她嘴里塞了颗枣,小饕餮哪里能想到有如此招数,枣子的清甜汁水在口中溢出来,当即让她顾头不顾尾地啃了起来。
阿勒抓着这机会问了句:“龙可羡好歹是她亲生女儿,怎的落到这般模样?”
其中细处,老仆也摸不准,只知道一点:“二姑娘是在城郊庄子里出生的。”
那就是把小炮仗藏起来了,阿勒若有所思,直至感受到掌心下的皮肤微微鼓动,那两弧耳廓摸着就像猫耳朵,软得不像话,直往他掌心里挠,挠得阿勒不自然地收了手,问道:“老头儿明日能回来么?”
老仆收拾杯盏:“主子这回出门,没有半个月,怕是回不来,公子安心在家,把姑娘看好了,十个宵小也比不上你们一根毫毛。”
出门时,庭中草叶冷翠,尖梢颤颤凝着水珠,滴滴答答地敲打青石阶。
龙可羡把脑袋枕在小窗口,她看出了领地的区分,于是乖乖待在自己屋里,看他穿过中庭,遥遥地指了下自己。
阿勒跟老仆说的是窗纸,“那色儿不好,外头琉璃窗结霜,里边看着就要晃眼,换个水蓝色的来。”
***
翌日小雪,不上书塾。
穹顶是暗沉沉的冷灰色,寒风卷着雪粒,沿着重檐叠瓦低飞。
内院院门紧闭,书屋旁的耳房里,铜壶咕嘟着,腾起的热气里夹着几道竹条拍击声,老仆忧心忡忡,几乎想破门而入。
而龙可羡坐在书桌前,看着阿勒有一下没一下拿竹条敲打掌心,有些没睡饱的怔忪。
“小……咳,龙可羡。”阿勒把竹条插在腰带上。
龙可羡迷迷糊糊点头。
“嘴巴张开我瞧瞧。”他弯身,捏住龙可羡下巴。
小孩儿不懂得收敛力道,捏得有些重,龙可羡本来就薄的颊肉陷无可陷,无意识地张了口,紧跟着嘴里探来个硬东西。
龙可羡噎得难受,呜呜地往后缩。
“别动。”阿勒从袖中掏出根脆骨,筷子粗细,指头长短,卡住她唇沿,仔细往里看。
一圈细密的珍珠小牙中躺着尾红鱼,喉咙深处吊着两点小肉团,因为呜咽而微微地颤着。
阿勒再凑近些,想要看看喉咙,刚拉近,那尾静静躺着的红鱼就骤然紧缩,他下意识地收手,险险地从两排牙齿中逃过一截。
“你……”
龙可羡面无表情,眼圈儿通红,“咔嚓咔嚓”地咬断吃掉了软骨。
算了,想来不是喉咙损伤,那就是没人教,不会讲,阿勒拿竹条点点桌面:“你我前日在廊下撞见时,你唤了我声哥哥。记得吗?哥哥。”
龙可羡听见熟悉的词,琢磨片刻,磕磕巴巴说:“哥,哥哥?”
“是了!”阿勒猛一拍掌,这一下把自己拍得重,掌心腾了片红色,但他不在意,“前日让你喊,怎的不喊?”
龙可羡又不懂了。
阿勒绕桌子走了一圈,心说急不得:“就从这开始,再喊一遍,哥哥。”
龙可羡没喊顺,不愿再开口了,把嘴闭得死紧。
“?”什么毛病,阿勒丢掉竹条,把准备好的一碟子糕点移过去,在龙可羡双眼灼灼地抬手过来时,又咻地收回来,慢悠悠地点一下桌面。
“讲好了,才有奖励,再来一遍,哥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