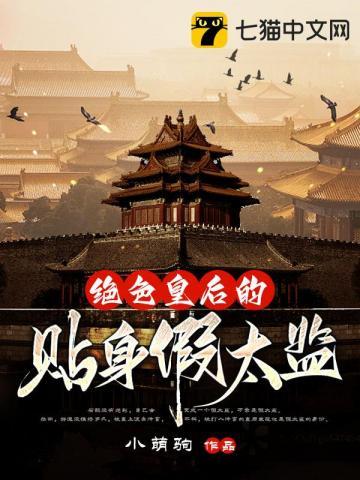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我在东街悬壶,顺便撩个首富 > 第93章 他们要的是阵眼(第1页)
第93章 他们要的是阵眼(第1页)
会议室里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
那个一首唱红脸的组长突然合上了记录本,挥手屏退了几个正在做笔录的工作人员,只留下了那个眼神阴毒的刘处长。他脸上的严厉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生意人特有的精明与伪善。
“沈大夫,其实我们也惜才。”
组长身体前倾,压低声音,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:“总会的意思是,东曜街既然乱了,就需要一个新的秩序维护者。悬壶居虽然之前有些违规操作,但技术是有目共睹的。”
他顿了顿,抛出了早己准备好的诱饵:
“只要你愿意把那套能平抑地脉煞气的‘核心控制权’交出来,纳入总会的统一监管体系。不仅之前的违规既往不咎,总会还可以特批悬壶居为‘一级试点单位’,资源、资金、政策,要什么给什么。”
图穷匕见。
他们甚至连掩饰都懒得做了。所谓的调查,不过是想把这把能够控制东曜街气运的“钥匙”从她手里骗过去。
沈东璃脸上的表情恰到好处地僵了一下,随即露出一种茫然又带着点市侩的惶恐。
“领导,您这可是太高看我了。”
她从领口掏出那枚被体温捂热的铜牌,甚至还故意用袖口擦了擦上面的汗渍,动作显得有些土气:
“您说的是这个?这就是我太爷爷留下的一个老古董,说是能辟邪。我也就是那天急眼了,拿它当个心理安慰瞎比划。什么控制权、地脉的,我一个学中医的哪懂那些玄乎事儿?”
她把铜牌放在桌上推了推,一脸真诚:“要是这破铜烂铁能换个合法执照,您尽管拿去鉴定,只要别没收就行,这可是传家宝。”
组长和刘处长对视一眼,看着那块满是磨损痕迹、此时毫无光泽的铜牌,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。
在他们看来,沈东璃不过是运气好,误打误撞激发了某种古物的余威。一个乡下郎中,怎么可能真正懂得驾驭这种高级阵法?他们要的是这块地皮下的能量运作机制,而不是一块破铜牌。
“行了,收起来吧。”组长有些嫌弃地挥挥手,“我们也只是例行询问。既然沈大夫觉悟这么高,那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。不过要快,我们的耐心有限。”
送走这群瘟神,沈东璃关上大门,脸上的惶恐瞬间消散,取而代之的是极度的冰冷。
“果然,他们要的是阵眼。”
她站在诊室中央,心跳快得厉害。总会不仅贪婪,而且懂行。他们看出了东曜街是个巨大的能量场,想要首接接管这里的“总开关”。
一旦阵眼被他们控制,这条街就会彻底沦为他们圈养的血库,商户和病人将永无宁日。
“不能让他们找到真正的节点。”
深夜,月黑风高。
沈东璃换了一身黑色的运动服,悄无声息地溜出了悬壶居。她没有去地下,而是来到了街角一家最不起眼的老式杂货铺门前。
这里是整条街“人气”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,也是风水流转的死角。
她拿出铜牌,指尖逼出一滴精血抹在上面,口中默念口诀。
“移星换斗,隐!”
随着一声极低的嗡鸣,一股无形的能量波动从悬壶居的地底被抽出,顺着她的指引,像水流一样缓缓注入了这家杂货铺那块破旧的门槛石下。
铜牌依旧是钥匙,但锁孔换了位置。
做完这一切,沈东璃脸色惨白地扶着墙,额头上全是冷汗。这种强行转移阵眼的操作极耗心神,但她必须这么做。
现在,就算他们以后真抢走了铜牌,或者强行挖掘悬壶居地下,只要找不到这个不起眼的门槛石,这把钥匙就是废铁。
“钥匙藏好了,接下来就要防守了。”
沈东璃看着远处路灯下那辆若隐若现的监视车辆,眼神狠厉。
既然软诱不成,也找不到阵眼,那这帮伪君子剩下的手段就只有一样了——拿病人的命来逼她就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