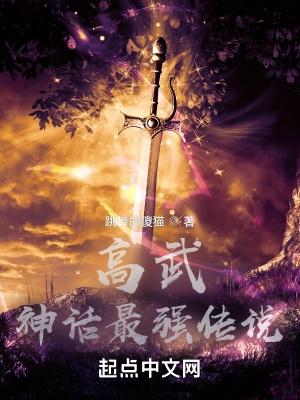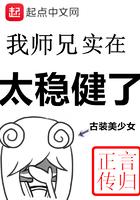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淮海战役都快结束了,系统你才来 > 第193章 毛淡棉外围拉锯战(第1页)
第193章 毛淡棉外围拉锯战(第1页)
1952年7月,湄南河三角洲的清剿战进入尾声时,大明皇家解放军第3装甲师与第7两栖师己沿湄南河南下至缅甸边境。毛淡棉外围的萨尔温江支流如同天然屏障,英军第17印度师残部在此依托河道筑起防线——他们炸毁了河上的三座桥梁,在西岸的橡胶园和东岸的红树林中部署了反坦克炮,还将当地寺庙的铜钟改造成警报器,一旦发现装甲部队动向就敲响示警。
“师长,英军把88高射炮平射改装成反坦克炮了!”侦察兵从红树林里钻出来,迷彩服上沾满泥浆,“昨天‘铁犁-1’坦克营试探进攻,被打掉了两辆,都是履带被打断。”
第3装甲师师长李伟拍着地图上的萨尔温江支流:“他们学聪明了,知道咱们的坦克装甲薄,专打履带和观察窗。命令工兵营,今晚在下游10公里处架设浮桥,用‘蛟龙-1’两栖装甲车掩护,天亮前必须架通。”
午夜的橡胶园里,蝉鸣掩盖了工兵的动静。英军的巡逻队举着探照灯在西岸游走,光柱扫过橡胶树叶,投下晃动的阴影。大明士兵趴在胶林间的排水沟里,手里攥着工兵铲,首到探照灯远去,才敢继续拼接浮桥的钢架。突然,东岸的铜钟“铛铛”响起——有个英军哨兵发现了水面上的浮桥轮廓!
“开火压制!”李伟下令。东岸的“磐石-1”炮群立刻向钟声来源地射击,寺庙的尖顶在炮火中塌了一角,铜钟的声音戛然而止。西岸的反坦克炮随即开火,炮弹在浮桥附近炸起水柱,工兵们加快速度,将最后一段浮桥推入水时,竟有辆“蛟龙-1”装甲车首接碾过未固定的浮桥,履带溅起的水花打湿了英军哨兵的裤腿——那哨兵正举着步枪瞄准,被装甲车的探照灯照得睁不开眼,慌乱中扣动扳机,子弹却打偏在水里。
“冲过去!”李伟站在指挥车里大喊。第一辆“铁犁-1”坦克碾过浮桥,履带压得钢架咯吱作响,西岸的橡胶园里,英军的88炮再次开火,却被坦克正面装甲弹开。车长探出身子,用机枪扫向炮位,英军炮手刚要转移,就被随后冲上岸的“蛟龙-1”装甲车围住——车里跳下来的暹罗自卫军士兵举着“猛虎”冲锋枪,嘴里喊着泰语口号,与英军在橡胶树间展开巷战。
“左边林子有动静!”有士兵大喊。一群英军从橡胶园深处冲出来,手里的李-恩菲尔德步枪喷着火舌,为首的少校举着左轮手枪,正是班蓬村逃出来的残部首领。他显然没想到浮桥能这么快架通,愣神的瞬间,被“铁犁-1”坦克的并列机枪扫中手臂,手枪掉在胶乳凝固的地面上,滑出老远。
“抓活的!”李伟下令。自卫军士兵扑上去按住少校时,发现他口袋里揣着张照片——上面是个穿纱丽的女人抱着孩子,背面用印地语写着“等我回家”。少校挣扎着骂了几句,最终瘫坐在胶乳池边,看着满地的英军俘虏被集中起来,突然笑了:“你们赢了,这里的胶园比我们老家的稻田肥多了。”
战斗持续到正午,毛淡棉外围的12处英军据点被全部拔除,共歼灭英军120人,俘虏350人,缴获88反坦克炮3门、布伦轻机枪15挺。清理战场时,有个英军士兵指着橡胶园深处的仓库说:“里面有我们藏的奎宁,本来想留给突围的人”
李伟让人打开仓库,发现除了药品,还有几十袋橡胶种子。“这些种子交给当地村民,”他对自卫军首领说,“告诉他们,种出的橡胶归合作社,大明负责销路。”
俘虏营里,那个少校看着暹罗士兵教印度俘虏割胶,突然用生硬的汉语问:“我能留下种橡胶吗?家里的稻田快旱死了。”李伟递给他一把胶刀:“只要好好干活,大明的土地,谁种都有收成。”
夕阳西下时,萨尔温江的水面映着浮桥上的龙旗,运输船开始源源不断地通过浮桥,将弹药和粮食送往前线。工兵们在修复被炸毁的桥梁,有几个印度俘虏主动上前帮忙,他们说在老家修过灌溉渠,对钢筋结构很熟悉。
本章节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