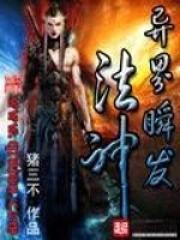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安史之乱:我手握十万兵马 > 第141章 镜中双影一诏两心(第3页)
第141章 镜中双影一诏两心(第3页)
“一石二鸟之计,”薛七郎的声音里满是杀气,“既能彻底毁掉您的名声,又能将太上皇也拖下水,让当今圣上父子猜忌,河北与朝廷彻底决裂。他们好坐收渔利。”
听完禀报,赵襦阳脸上非但没有怒气,反而浮现出一丝冰冷的笑意。
“他们想画,就让他们画好了。”他吩咐道,“去,把我当初与裴参军一同巡视流民营的旧画取来。另外,再找城中最好的画师,连夜给我画一幅新的。”
薛七郎不解:“画什么?”
赵襦阳的目光穿过窗棂,望向长安的方向,嘴角勾起一抹讥诮:“就画我赵襦阳,身着布衣,跪于太上皇驾前,双手高举一本民册。画得越卑微,越恭顺越好。”他顿了顿,声音变得愈发寒冷,“画好之后,立刻制成千百份,传遍关中、河北各州。他们要画我图谋不轨,我便画自己俯首低头。我倒要看看,是他们伪造的密室阴谋传得快,还是我这幅跪献民册的忠心图,传得更广!”
九月廿九,启程之日。
天还未亮,恒州城内的百姓便自发地走出家门,手持灯笼,汇聚在长街两侧,沉默地为他们的节度使送行。
那一片连绵不绝的灯海,一如他上次出征前一样,温暖而明亮,是这乱世中最坚实的力量。
赵襦阳立于车前,并未立刻登车。
他转身,亲自接过亲兵抬来的那块“民本可依”的匾额,在万众瞩目之下,命人将其高高悬挂在了恒州城的鼓楼之上。
金色的阳光刺破晨雾,照在西个大字上,熠熠生辉,仿佛一种无声的宣告。
做完这一切,他从怀中取出了那份肃宗的密谕。
在无数道惊疑不定的目光中,他走到一个燃烧的火盆前,竟当众将那份代表着天子意志的诏书,投入了熊熊烈火之中。
纸张瞬间卷曲,变黑,被火焰吞噬。
裴玉筝策马立于他身侧,面纱下的双眸写满了震惊,她低声急问:“你为何要毁了它?这可是……”
赵襦猴没有回头,只是望着那跳动的火焰,仿佛在看一场早己注定的结局。
风将他的声音吹得有些飘忽,却异常清晰:“一封诏书,劝我安分守己。一块匾额,许我安抚万民。我若拿着肃宗的密诏去凤翔,便是向太上皇示威;我若只奉太上皇的匾额,便是对当今圣上的不敬。无论执其一端,必失其二。”
火焰渐渐熄灭,唯余灰烬如黑色的蝴蝶,被风卷起,飞向空中。
他终于转过身,目光扫过那一片无边无际的灯海,扫过每一张质朴而信任的面孔,最后望向远方那座名为长安的城池,声音沉静而有力。
“如今,我毁掉密诏,将匾额悬于城头,就是要让天下所有人都看见——我赵襦阳,谁都不信。”
“我只信这恒州城,这千万盏灯,这万千张口。”
风势陡然转急,吹得鼓楼上的匾额嗡嗡作响。
车队缓缓启动,消失在官道的尽头。
城墙之上,陈砚舟目送着最后一骑的背影没入地平线,心中那份因节度使离去而产生的空虚与不安,被一股莫名的寒意迅速填满。
他下意识地握紧了腰间的刀柄,环顾着这座因为主心骨的离去而显得有些过分安静的城池。
城门在车队离去后缓缓关闭,发出的巨大声响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。
然而,在这沉重的闭合声之后,一种异样的死寂,开始在秋日的寒风中悄然蔓延。
夜幕,将比以往任何时候,都来得更早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