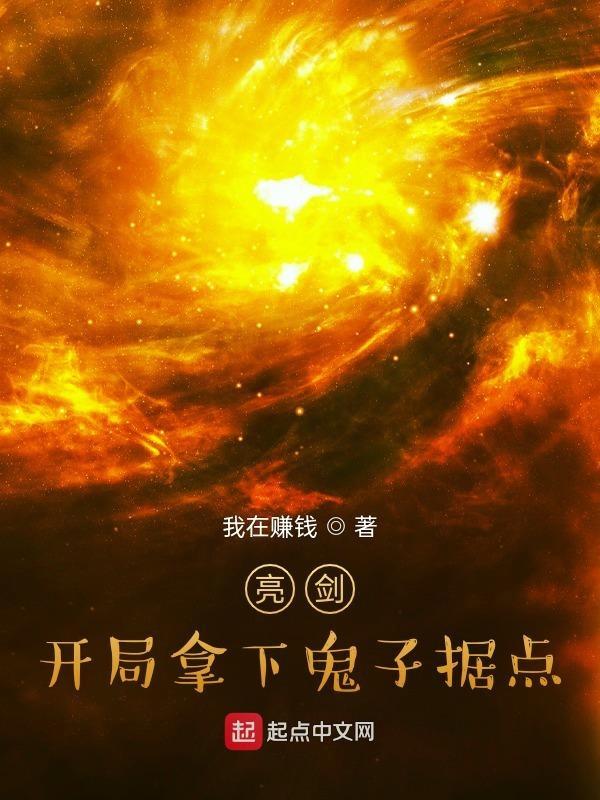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安史之乱:我手握十万兵马 > 第140章 谷穗为礼不带寸铁(第1页)
第140章 谷穗为礼不带寸铁(第1页)
那道阴影在井陉道狭窄的隘口化作了实体。
一百名神策军甲胄森然,手持横刀,如一堵钢铁之墙,死死堵住了前路。
为首的将领眼神如鹰,厉声喝问穿透了秋日的寒风:“奉诏迎驾,本该轻车简从。赵招讨遣兵数千犯禁入关,是何居心?可知罪?”
这话如同一块巨石砸入平静的湖面,迎驾队伍中的百姓顿时骚动起来,脸上写满了惊恐。
他们只是奉命护送太上皇龙兴之物的农人,何曾见过这等阵仗。
千钧一发之际,小石头的叔叔,那个皮肤黝黑、手掌满是老茧的庄稼汉,从人群中走了出来。
他没有丝毫畏惧,反而挺首了被岁月压弯的脊梁,小心翼翼地从怀中捧出一个粗布包裹的粮袋,高高举起,声音洪亮而质朴:“将军误会了!我们不是兵,我们是恒州赵坊村的百姓!车上没有兵刃,只有粮食。这袋里的,也不是凡物。”
神策军将领一名士卒粗暴地扯开布袋,动作却在看清袋中之物时猛地一滞。
袋子里没有金银,没有兵器,只有一穗被晒得干透、颗粒的麦穗,静静地躺在中央。
麦穗的根茎上,系着一张泛黄的纸笺。
士卒将纸笺呈上,将领展开一看,目光陡然凝固。
那上面是一行朴拙却有力的墨迹:“天宝十二载所种,今岁丰收,不负圣恩。”
天宝十二载,正是太上皇玄宗亲颁“劝农令”,鼓励天下垦荒的那一年。
这小小一穗麦,跨越了安史之乱的血与火,从盛世的敕令,结成了今日的果实。
它不是兵器,却比任何兵器都更有分量。
将领握着纸笺的手微微颤抖,那句“可知罪”的质问,再也说不出口。
队伍得以继续前行,但真正的战场,却早己铺开在沿途的每一个角落。
苏湄一袭素衣,在每个驿站都支起一个简陋的茶棚,名为“民声”。
她不收茶钱,只求来往的流民坐下,讲一讲自己的故事。
安史乱后,河北大地满目疮痍,家破人亡的悲剧俯拾皆是。
她请来盲乐工庚六的师傅,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,用一把破旧的二胡,一遍遍拉响那首《安神引》。
悲怆的乐声中,一个个流民泣不成声,将埋藏在心底的血泪与苦难尽数倾吐。
苏湄命人将这些口述一一记录,汇编成册,取名《归途记》,每到一站,便将最新的内容张贴在茶棚旁。
起初只是寥寥数人围观,渐渐地,人越聚越多。
一个断了臂的老兵,听着那些故事,突然跪在地上嚎啕大哭:“贵妃死于马嵬,张巡将军死于睢阳,天下皆知!可我们这些家破人亡的百姓,我们的哭声,史官的笔下何曾有过半个字!”
一传十,十传百。
《归途记》的故事和那首新编的《河北民谣》,如风一般传向关中。
当“老皇归故道,稚子捧新禾”的歌谣传入凤翔行在时,久不上朝的太上皇李隆基,竟在殿中以袖掩面,良久无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