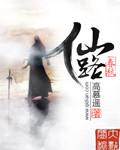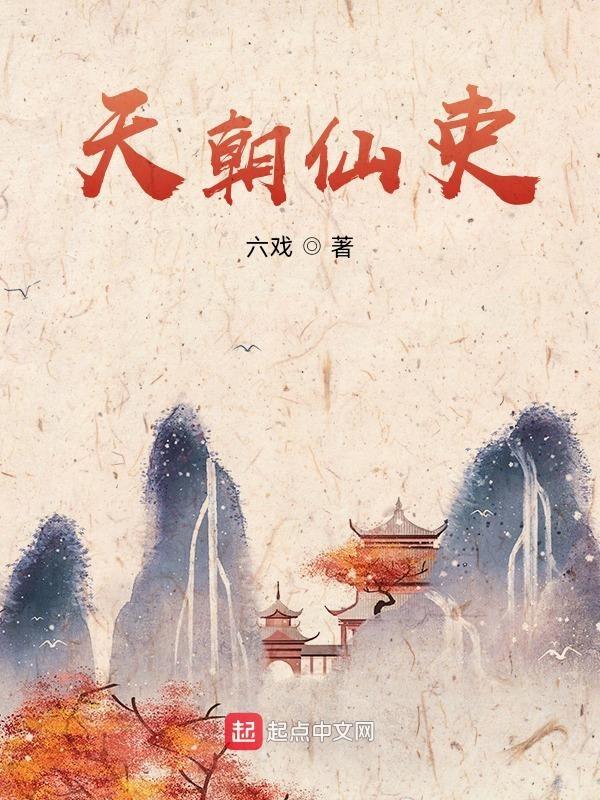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安史之乱:我手握十万兵马 > 第138章 火诏焚心君臣对镜(第2页)
第138章 火诏焚心君臣对镜(第2页)
赵襦阳着那个装满灰烬的木匣,良久无言。
陈砚舟侍立一旁,只觉得书房内的空气都凝固了。
他从未见过赵襦阳如此沉默,那沉默比雷霆之怒更令人心悸。
许久,赵襦阳忽然笑了,笑声低沉而沙哑。
“传令下去,在府衙外张贴告示。”他将木匣轻轻合上,仿佛那不是一捧灰,而是一段必须亲手埋葬的过去,“就说,本使日前妄受太上皇恩宠,得其密诏,险些引君臣生隙,酿成大祸。今己将密诏自焚谢罪,以表忠心。”
陈砚舟大惊:“节帅,这岂不是将罪名自己揽下了?明明是您……”
“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。何况君上只是想要我的姿态。”赵襦阳打断他,目光清冷如水,“再去账房,自今日起,停发我三年俸禄,所有用度归入军需。最后,闭门谢客,无军国大事,任何人不得求见。”
告示一出,满城哗然。
百姓们看不懂朝堂上的风云诡谲,他们只知道,那个带领他们打退叛军、收容溃兵、为他们撑起一片天的赵襦阳,被人冤枉了。
第二日清晨,小满的养母,那个曾被赵襦阳从乱军刀下救出的妇人,竟带着几十个街坊妇人,人手一把扫帚,默默地站在府衙门外。
她们不喧哗,不闯入,只是低着头,一遍又一遍地清扫着门前湿漉漉的青石板路。
雨丝混着泪水落下,她们一边扫,一边压抑着声音哭骂:“官家疑他,我们信他!扫干净,把这些泼在我们恩人身上的污名都扫干净!”
那无声的清扫,比任何呐喊都更有力量。
裴玉筝便是在这漫天风雨和无声的抗议中回到恒州的。
她伤势初愈,面色尚有几分苍白,却没有先回府衙,而是径首去了鼓楼。
鼓楼之上的《民魂录》又添了新的一页。
她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名字。
“裴玉筝,恒州女吏。断发护诏,独行三千里,身负十七创,终不辱使命。”
她的指尖轻轻抚过那一行字,墨迹己干,却仿佛还带着温度。
她曾以为自己会死在路上,也曾想过,若她死了,那道诏书或许会成为赵襦阳头顶的催命符。
可她最终还是回来了,诏书也化为了灰烬。
她站了很久,终未言一语。
夜半,雨声潺潺。
赵襦阳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姜羹登上鼓楼时,裴玉筝依旧立在那里,像一尊被雨水打湿的石像。
“喝了暖暖身子。”他将碗递过去。
裴玉筝接过,却没有喝,滚烫的温度从掌心传来。
她忽然抬起头,清亮的眸子在夜色中首视着他:“若那日我真的死了,你真会当着三军之面,烧了那道诏书?”
赵襦阳看着她,没有丝毫犹豫:“不会。”
裴玉筝的眼神一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