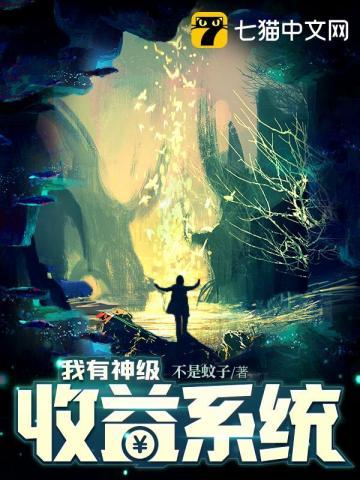大燕小说>鬼灭之刃千年的执念 > 第19章江户时代出道(第3页)
第19章江户时代出道(第3页)
然后是更精细的妆容。粉敷得更白,唇点得更小更红,眉毛被修整描绘成柔婉的弧度。每一笔,都像是在她原有的面孔上覆盖一层新的面具。
最后是衣服。她们取来一件崭新的粉色格纹、印着细碎樱花图案的丝绸和服,颜色娇嫩,图案浪漫,是典型的、迎合普通审美的游女装扮。
林子看着那粉嫩的颜色,胃里一阵翻涌。这颜色与她记忆中的冰雪、与战斗、与死亡……格格不入。
她们帮她一层层穿上,系上浅黄色、绣着暗纹的高级腰带,在后背打上复杂的太鼓结。腰带勒得很紧,让她呼吸都有些困难。最后,一双崭新的、鞋底颇高的黑漆涂面木屐被放在她脚下。
“来,试试看,若雪姑娘。”一位年长的姐姐笑着催促。
林子僵硬地抬起脚,穿上木屐。高底让她本就不习惯和服步伐的身体更加不稳,她必须小心翼翼地控制平衡,才能避免摔倒。
走起路来,木屐发出“咔嗒、咔嗒”的清脆响声,每一步都敲打在她的神经上。
她被扶到一面巨大的铜镜前。
镜中的女子,高耸的发髻,苍□□致的妆容,娇艳的和服,华丽却束缚的腰带,踩着高高的木屐……陌生得令人窒息。
所有属于“林子”的痕迹——那些战斗留下的细微疤痕(已淡化),那份属于剑士的挺拔与警觉,甚至是被迫成为鬼后残留的冷硬气质——都被这身华丽的装扮巧妙地掩盖或扭曲成了另一种“风情”。
她看着镜中的自己,眼神空洞,没有任何情绪。心底最后一丝波澜,似乎也在这繁琐的装扮过程中,被彻底磨平了。
像什么呢?
啊,对了。像一个匠人精心制作、披挂着华美绸缎和饰品的提线木偶。外表光鲜亮丽,引人注目,内里却空空如也,一举一动都被无形的线操纵着。
松岛总管不知何时也进来了,满意地打量着镜中的“作品”,点点头:“不错,很有游女的样子了。记住,若雪,从今天起,你就是‘露华屋’的游女若雪。你的言行举止,都代表着‘露华屋’的体面。好好准备,晚上还有几位重要客人点名要见你。”
林子(若雪)缓缓转过头,看向松岛,脸上挤不出任何表情,只是极其轻微地点了点头,喉咙里发出一声几乎听不见的:“……是。”
声音干涩,没有任何波澜。
松岛似乎很满意她这种“驯服”的状态,又嘱咐了几句仪态和应对客人的技巧,便离开了。
房间里只剩下林子和两个帮忙的姐姐。她们开始收拾东西,嘴里还小声议论着哪位客人阔绰,哪位客人难伺候。
林子独自站在镜前,久久不动。木屐的鞋底很高,让她不得不微微仰着头,才能看清镜中的全貌。这个姿势,更像一个被展示的商品了。
她尝试着微微动了一下手指,指尖冰凉。又尝试调动了一□□内那被药物隐隐压制的、属于雪姬的冰寒气息,回应微弱而滞涩,如同被厚茧包裹。
华丽的衣服紧贴着皮肤,腰带勒着胸口,沉重的发髻压迫着颈椎,高高的木屐让她脚踝酸痛。
一切都在提醒她:你是若雪,是游女,是“露华屋”的财产,是待客的玩物,是搜寻“蓝色彼岸花”的工具。
她缓缓地、极其缓慢地,对着镜子,扯动嘴角,练习了一个标准而空洞的、属于游女“若雪”的微笑。
镜子里的美人笑了,眼波却没有丝毫暖意,只有一片冰冷的麻木。
自我,早已在一次次被迫的改造和压抑中,变得支离破碎,最后只剩下这具被华丽衣装包裹的、名为“若雪”的空壳。
她移开目光,不再看镜中那个陌生的自己。窗外,吉原的喧嚣隐隐传来。夜晚即将降临,属于“游女若雪”的“工作”,才刚刚开始。
而她,除了继续扮演好这个提线木偶的角色,在这更华丽也更危险的牢笼中活下去,似乎已别无选择。
至少,在找到“蓝色彼岸花”或彻底毁灭之前,她必须“活”着。